没有人从当时的传媒中得知,就在10月28日早晨,在渤海湾烟台海域,也就是在发生过"盛鲁号"、"大舜号"海难的地方,又发生了一起重大沉船事故,"通惠号"客货混装船在八九级大风中出航、起火、沉没,"至当天中午,共救起5位幸存者,此后打捞起来的遇险者,全都是尸体"。"全都是"是多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无从知道,我至今无从知道!
这次海难事故,我是在2001年11月12日出版的《三联生活周刊》上读到的。我每天的工作要翻阅数十种主要报刊,只在这家发行量并不大的"生活周刊"上读到这个消息。据该刊报导,当地记者报怨说:有了两次处理海难的经验,"当地部门处理得更熟练了",即封锁消息更严、对记者看得更紧。采访者被盯梢,幸存者被贴身"关照",死难者家属被软硬兼施加压,都是题中之义。当事人(船主、管理部门、地方政府)之所以要这样封锁消息是顺理成章的:这船根本就不该投入营运,不该那样违章装载,不该在那样的天气出海,一旦诉诸舆论,就难免有人坐牢、丢官、受处分,而不能赔几万块钱了事。可是,我们的传媒为什么要与肇事者、责任人的立场保持一致呢?为什么不考虑惩前毙后防止类似悲剧重演呢?难道中国平民的命比不上阿富汗人宝贵?难道真的中国人之死只有与美国人搭上瓜葛才特别有价值,才会受到举国上下关注?
谁都明白,这都是控制报导权、操纵社会舆论的结果。正如时下在新闻业界内外流传甚广的一首歌谣所咏的:"舆论监督是条狗,天天蹲在'长'门口,'长'叫咬谁就咬谁,叫咬几口咬几口"。("舆论监督"四字在有些版本中被置换成具体栏目或节目,有的版本是"新闻记者"四字;至于"长"是报社社长、电视台台长、宣传部长、……并不重要,总之是长官)。"狗"的比喻,可谓穷形尽相。舆论监督,一般地说,不具观赏性,不是讨人喜欢的宠物,即不是叭儿狗,而是防盗撵贼的护院狗。但不论怎么样,良狗的特性是忠实于直接豢养它的主人,听命于主人。这种奴性正是中国人鄙视狗的缘故。以狗比新闻记者,喻所谓的"舆论监督",正是对记者缺乏独立人格、"舆论监督"一副奴颜媚骨的轻蔑和嘲谑。所谓"叫咬谁就咬谁",入木三分地刻划了"舆论监督"的势利与不公正;所谓"叫咬几口咬几口"则特别生动地表现了"舆论监督"的伪善--许多个案都是就事论事,糊弄百姓,即使历尽曲折平反的冤狱也就是处罚几个打手,幕后的主事者往往不去深究,连追问一句都不敢,还要奉送"高度重视"、"严肃处理"之类的恭维。
"舆论监督"为什么会堕落成"狗"呢?
因为我们没有赋予它独立的品格,它不是属于人民大众的社会公器,而只是少数人掌控的政治工具。如果是社会公器,它就应只服从于宪法,以它自身的方式服务于公众的利益,只认事实而不应屈从于某些人的意志与权力。
为此,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传媒独立的品格,或者说它们特有的价值是什么,它们的使命和义务是什么?
其实,马恩关于报刊的使命、义务、职责曾有十分明白的论断。1848年7月5日,《新莱茵报》发表《逮捕》一文,揭露了宪兵和科伦检察机关的非法行为,为此马克思、恩格斯等人遭到控告。马克思在陪审法庭上发表演说,为自己及伙伴辩护。他义正辞严地说:"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无处不在的喉舌。""首先,报刊的义务正是在于为它周围左近的被压迫者辩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P274-275)即使是这个资产阶级的法庭也不能不承认马克思所持的原则是正确的,法庭最后宣判所有被告无罪。在另一个场合,马克思说:"在我看来是报刊的首要职责,即揭发招摇撞骗的职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755页)马克思此言的背景是,他的同志李卜克内西向《总汇报》提供了一篇指控福林特是法国募的文章,福林特向《总汇报》提起诉讼,而文章作者布林德拒不承认自己是作者。马克思站出来,向《总汇报》提供证明布林德是作者的材料,在致《总汇报》编辑的信函中他讲了上面的话。马克思尊重的是事实,至于党派利益、私人交谊等等不能构成他回避事实、掩盖真相的借口。也许有聪明人会说马克思缺乏"政治意识",但在他看来,违背良知讲昧心话的人根本不配谈政治。今天我们讲传媒工作者要有"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这都是十分正确的、非常必要的。问题不在辞句而在内容。我想,所谓"政治意识"就是要"立党为公",不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所谓"大局意识",就是从坚持维护人民大众根本利益的政治原则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目标出发,不掩恶不护短,即使"挥泪斩马谡"也在所不惜;所谓"责任意识"就是实事求是,报喜不吹牛不撒谎说话负责,揭短不夸大不诬枉经得起法庭调查。这种理解是否恰当可以斟酌,但有一点,应当是可以肯定的,即新闻报导、舆论监督中的所谓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决不应是权谋意识、权术意识、欺瞒意识;避重就轻,避实就虚、欺善怕恶、欺软怕硬,搞官官相护、欺上瞒下、"愚民政策"那一套,决不是正大光明者所应为,决不符合共产党人的信念。
为什么现在新闻工作者不敢理直气壮地讲自己是人民的喉舌呢?如上所述,马克思在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庭尚可以这么讲,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在人民共和国的阳光下倒不可讲了,岂非咄咄怪事!不错,在中国,传媒特别是机关报,是党的喉舌,但党的喉舌并不等于"长"的喉舌,并不是每一级的宣传部长和书记都自然而然地是代表党的。为什么要把党与人民对立起来呢?毛泽东说过: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责任,每句话每个行动都是符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就要改正。既然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那么,从政治层面言,讲人民的喉舌、讲人民的利益、讲对人民负责不就是管总的吗?具体到组织管理层面,毛也讲过: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离开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我们要相信传媒与舆论的主管机关,同时也要相信广大的新闻工作者,大家都要反腐倡廉,也都不希望天下大乱。何况,全国重要的媒体里都有党组织,都是党员干部主事,为什么不可以放手让他们依法进行舆论监督呢?
如果关于传媒与舆论监督的这些指导思想、管理原则不理顺,新闻传媒就脱不了狗的属性,"舆论监督"要具有公信力,要在安邦治国中发挥重要作用,是根本不可能的。
顺便提到一个可笑又可气的新闻细节。也是2001年10月下旬,据广东传媒报导,19岁的湖北省通城县少女刘荷到深圳市去打工,尚未找到工作而因"三证"不全被宝安区收容遣送站收容,在被收容期间,被陌生人"冒领"出去惨遭凌辱。收容站工作人员与"冒领"者是什么关系,有什么交易有待调查;起码,他们的失职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当记者去采访有关管理部门的负责人时,先是被拒绝,后又被义正严辞地教导:记者应该坚持正面宣传,多报导他们是怎样为群众排扰解难的!这些人分明做了伤天害理的事,却这般振振有词,他们的歪理邪说是从哪儿来的灵感和底气?
这几年流传著一句顺口溜叫"防火防盗防记者"。这个"防记者"当然是防搞舆论监督的记者(对于吹喇叭抬轿子当跟班的记者,他们不仅不防,或电话"召记",领导未行秘书先通知新闻单位派人,或高价拉请,提供吃喝玩乐一条龙服务,"诱以官、禄、德"的花样不一而足)。"防"的手段有多种。首先是牢牢控制本地的新闻传媒,严令传媒老总这个不准报导那个不准披露,违者即摘掉乌纱帽或砸他的饭碗;对于上级和中央传媒的记者,则授意本地有关人员不得接受采访,有的地方甚至由政法委另外专门制了记者证,只认他们这个证,不信国家新闻出版署制发的证。文明的设防手段是封锁现场和消息来源,不文明的就干脆采用暴力驱赶殴打记者,抢夺记者拍摄的音像资料。当然,威胁受访的群众也是其中一招。记者的人身安全越来越没有保障:揭发山西运城地区领导制造虚假的节水渗灌工程的记者高勤荣身陷囹圄;为主持正义曝光海南一起卖淫嫖娼案的记者刘洪以被逼疯;重庆女记者罗侠在采访现场被人打成重伤……一起接一起伤害记者案令人发指,也令从事舆论监督的人心寒。如果还是说"新闻记者是条狗",则毫不夸张地讲,从事舆论监督的记者在某些官员眼中是威胁他们官运的恶狗、野狗,无人保护的记者则很像一条条丧家狗。CCTV的记者在《偷拍实录》一书的后记中写道:"很'牛'的中央电视台记者,带著偷窃般的心态,忍著内心的愤怒,以一名弱小平民百姓的身份,目击著欺骗、凌辱、威胁、谩骂、违法、乱纪等一系列'精彩表演',这是中国新闻史上很特殊的一种现象。"
之所以如此,不需要多少理论水平和政治智慧,谁都知道,这是如今中国的新闻记者缺乏法律保护的必然结果。当事人不希望自己的丑事变丑闻,当官的要维护他们的所谓政绩和政治形象,至少是避免因千夫所指而下台,这都是人之常情。奇怪的倒是,我们天天在喊"依法治国",为什么就是迟迟不肯出台"新闻法"或"舆论监督法"?
"新闻法"已经呼唤有年,10多年来几乎每年两会期间都有提案提出。问题洞若观火,大家都是明白人。据《中国青年报》2001年11月9日报导:"全国人大新闻局副局长沈掌荣对过去几年中发生的严重侵犯记者人身权、采访权的恶性事件记忆犹新。他特别提到福州记者顾伟因采访老虎机赌博事件,被打黑枪的事�I蛘迫俪庵?#039老虎机背后有真老虎'。
国务院法制局法制司司长青锋剖析新闻采访权屡遭侵犯的原因认为,这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各方利益冲突的必然体现。
青锋说,新闻采访权不是行政权力,也不是司法权力,它是公众知情权。但记者行使新闻采访权时,由于没有明确强有力的法律保障,采访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对方的好恶。尤其行使舆论监督的记者,必然激起那些既得利益者的痛恨,轻则设置重重关卡阻碍采访重则拳脚相加。
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厅孙加瑞一针见血地指出,记者在新闻采访时受到侵害,与普通公民权受到侵害的保护方法应该有所差别。因为公众知情权是建立在新闻采访权基础上的,新闻采访权受到暴力干涉,整个社会公共利益就会受到伤害,因此对新闻采访权需要从法律上加以特别的明确保护。对侵犯记者人身权的案件,不宜按普通案件或刑事案件来处理,应加大处罚力度。"
新华社在点评罗侠被殴打事件时指出:"引人关注的是,记者罗侠的遭遇并不是偶发事件。为什么有些行凶肇事者气焰嚣张,无所顾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些事件并没有得到公正的处理;有些肇事者并没有依法受到应有的处罚;对触及'痛处'的新闻采访,有的地方和部门更是明里暗里纵容和支持阻扰采访的行为。这种情况不容再继续下去了。
新闻单位行使舆论监督就是行使人民的民主权利,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和全社会的支持。保护记者的采访权,就是保护正义的监督权、公众的知情权和人民的民主权利。"(见上海《新民周刊》2001年第45期的转载)
他们说的难道有什么不对吗?难道还有什么反驳理由更有力而不宜摆上桌面吗?
可以肯定,中国的新闻记者是务实的,他们并未想曝光水门事件、拉链门事件、五角大楼越战文件那样高层新闻,他们不过是想配合党和政府反腐肃贪、反对吏治腐败与司法腐败、打击假冒伪劣产品。他们只是想在从事这样的舆论监督时,人身安全不受侵犯,他们愿意承担编造假新闻诬人清白的法律后果,他们只是希望法律明确什么人什么事有权拒绝采访,什么人什么事不能拒绝采访……不论他们怎样想,法律总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总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制定的。
有鉴于此,对于"新闻法"迟迟不能出台,我只能说:匪夷所思。
参与国家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是宪法赋予共和国每个公民的权利;舆论监督是公民这种参与权的具体体现,新闻记者应当是国家的主人、自己的主人,不是狗,不是谁豢养的家狗,也不是任人猎杀的野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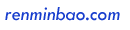
























 打印机版
打印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