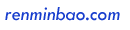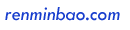|
【人民報消息】翻開2001年10月下旬的報刊,可見我們的新聞輿論中有許多引人注目的熱點和焦點:APEC會議在中國上海召開,飛機、警察、警犬是怎樣保衛高官們的,他們的唐裝是何人設計、他們的宴會吃的幾道什麼菜:"我們贏了",與米盧教練"零距離"接觸的那個女記者李響,他們到底是什麼關係,李所在報社允諾給她月薪50萬是否合理;今天美國飛機又轟炸了哪裏,又有幾個阿富汗平民被炸死?關於阿富汗戰事,我外長是怎麼說來著,反恐打擊要有準確的目標,避免平民傷亡……這一切,當然都值得報導,因爲有人感興趣,想知道,可營造歡樂祥和的輿論氛圍,或顯我人道立場、大國風範。 沒有人從當時的傳媒中得知,就在10月28日早晨,在渤海灣煙臺海域,也就是在發生過"盛魯號"、"大舜號"海難的地方,又發生了一起重大沉船事故,"通惠號"客貨混裝船在八九級大風中出航、起火、沉沒,"至當天中午,共救起5位倖存者,此後打撈起來的遇險者,全都是屍體"。"全都是"是多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無從知道,我至今無從知道! 這次海難事故,我是在2001年11月12日出版的《三聯生活週刊》上讀到的。我每天的工作要翻閱數十種主要報刊,只在這家發行量並不大的"生活週刊"上讀到這個消息。據該刊報導,當地記者報怨說:有了兩次處理海難的經驗,"當地部門處理得更熟練了",即封鎖消息更嚴、對記者看得更緊。採訪者被盯梢,倖存者被貼身"關照",死難者家屬被軟硬兼施加壓,都是題中之義。當事人(船主、管理部門、地方政府)之所以要這樣封鎖消息是順理成章的:這船根本就不該投入營運,不該那樣違章裝載,不該在那樣的天氣出海,一旦訴諸輿論,就難免有人坐牢、丟官、受處分,而不能賠幾萬塊錢了事。可是,我們的傳媒爲什麼要與肇事者、責任人的立場保持一致呢?爲什麼不考慮懲前斃後防止類似悲劇重演呢?難道中國平民的命比不上阿富汗人寶貴?難道真的中國人之死只有與美國人搭上瓜葛才特別有價值,才會受到舉國上下關注? 誰都明白,這都是控制報導權、操縱社會輿論的結果。正如時下在新聞業界內外流傳甚廣的一首歌謠所詠的:"輿論監督是條狗,天天蹲在'長'門口,'長'叫咬誰就咬誰,叫咬幾口咬幾口"。("輿論監督"四字在有些版本中被置換成具體欄目或節目,有的版本是"新聞記者"四字;至於"長"是報社社長、電視臺臺長、宣傳部長、……並不重要,總之是長官)。"狗"的比喻,可謂窮形盡相。輿論監督,一般地說,不具觀賞性,不是討人喜歡的寵物,即不是叭兒狗,而是防盜攆賊的護院狗。但不論怎麼樣,良狗的特性是忠實於直接豢養它的主人,聽命於主人。這種奴性正是中國人鄙視狗的緣故。以狗比新聞記者,喻所謂的"輿論監督",正是對記者缺乏獨立人格、"輿論監督"一副奴顏媚骨的輕蔑和嘲謔。所謂"叫咬誰就咬誰",入木三分地刻劃了"輿論監督"的勢利與不公正;所謂"叫咬幾口咬幾口"則特別生動地表現了"輿論監督"的僞善--許多個案都是就事論事,糊弄百姓,即使歷盡曲折平反的冤獄也就是處罰幾個打手,幕後的主事者往往不去深究,連追問一句都不敢,還要奉送"高度重視"、"嚴肅處理"之類的恭維。 "輿論監督"爲什麼會墮落成"狗"呢? 因爲我們沒有賦予它獨立的品格,它不是屬於人民大衆的社會公器,而只是少數人掌控的政治工具。如果是社會公器,它就應只服從於憲法,以它自身的方式服務於公衆的利益,只認事實而不應屈從於某些人的意志與權力。 爲此,我們首先要弄清楚什麼是傳媒獨立的品格,或者說它們特有的價值是什麼,它們的使命和義務是什麼? 其實,馬恩關於報刊的使命、義務、職責曾有十分明白的論斷。1848年7月5日,《新萊茵報》發表《逮捕》一文,揭露了憲兵和科倫檢察機關的非法行爲,爲此馬克思、恩格斯等人遭到控告。馬克思在陪審法庭上發表演說,爲自己及夥伴辯護。他義正辭嚴地說:"報刊按其使命來說,是社會的捍衛者,是針對當權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無處不在的眼睛,是熱情維護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無處不在的喉舌。""首先,報刊的義務正是在於爲它周圍左近的被壓迫者辯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P274-275)即使是這個資產階級的法庭也不能不承認馬克思所持的原則是正確的,法庭最後宣判所有被告無罪。在另一個場合,馬克思說:"在我看來是報刊的首要職責,即揭發招搖撞騙的職責"。(《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755頁)馬克思此言的背景是,他的同志李卜克內西向《總彙報》提供了一篇指控福林特是法國募的文章,福林特向《總彙報》提起訴訟,而文章作者布林德拒不承認自己是作者。馬克思站出來,向《總彙報》提供證明布林德是作者的材料,在致《總彙報》編輯的信函中他講了上面的話。馬克思尊重的是事實,至於黨派利益、私人交誼等等不能構成他迴避事實、掩蓋真相的藉口。也許有聰明人會說馬克思缺乏"政治意識",但在他看來,違背良知講昧心話的人根本不配談政治。今天我們講傳媒工作者要有"政治意識"、"大局意識"、"責任意識",這都是十分正確的、非常必要的。問題不在辭句而在內容。我想,所謂"政治意識"就是要"立黨爲公",不忘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所謂"大局意識",就是從堅持維護人民大衆根本利益的政治原則和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政治目標出發,不掩惡不護短,即使"揮淚斬馬謖"也在所不惜;所謂"責任意識"就是實事求是,報喜不吹牛不撒謊說話負責,揭短不誇大不誣枉經得起法庭調查。這種理解是否恰當可以斟酌,但有一點,應當是可以肯定的,即新聞報導、輿論監督中的所謂政治意識、大局意識、責任意識,決不應是權謀意識、權術意識、欺瞞意識;避重就輕,避實就虛、欺善怕惡、欺軟怕硬,搞官官相護、欺上瞞下、"愚民政策"那一套,決不是正大光明者所應爲,決不符合共產黨人的信念。 爲什麼現在新聞工作者不敢理直氣壯地講自己是人民的喉舌呢?如上所述,馬克思在資產階級國家的法庭尚可以這麼講,我們的新聞工作者在人民共和國的陽光下倒不可講了,豈非咄咄怪事!不錯,在中國,傳媒特別是機關報,是黨的喉舌,但黨的喉舌並不等於"長"的喉舌,並不是每一級的宣傳部長和書記都自然而然地是代表黨的。爲什麼要把黨與人民對立起來呢?毛澤東說過:我們的責任是向人民責任,每句話每個行動都是符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錯誤,就要改正。既然共產黨人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那麼,從政治層面言,講人民的喉舌、講人民的利益、講對人民負責不就是管總的嗎?具體到組織管理層面,毛也講過:我們應當相信羣衆,我們應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離開這兩條原理,那就什麼事情也做不成了。我們要相信傳媒與輿論的主管機關,同時也要相信廣大的新聞工作者,大家都要反腐倡廉,也都不希望天下大亂。何況,全國重要的媒體裏都有黨組織,都是黨員幹部主事,爲什麼不可以放手讓他們依法進行輿論監督呢? 如果關於傳媒與輿論監督的這些指導思想、管理原則不理順,新聞傳媒就脫不了狗的屬性,"輿論監督"要具有公信力,要在安邦治國中發揮重要作用,是根本不可能的。 順便提到一個可笑又可氣的新聞細節。也是2001年10月下旬,據廣東傳媒報導,19歲的湖北省通城縣少女劉荷到深圳市去打工,尚未找到工作而因"三證"不全被寶安區收容遣送站收容,在被收容期間,被陌生人"冒領"出去慘遭凌辱。收容站工作人員與"冒領"者是什麼關係,有什麼交易有待調查;起碼,他們的失職是無可辯駁的事實。當記者去採訪有關管理部門的負責人時,先是被拒絕,後又被義正嚴辭地教導:記者應該堅持正面宣傳,多報導他們是怎樣爲羣衆排擾解難的!這些人分明做了傷天害理的事,卻這般振振有詞,他們的歪理邪說是從哪兒來的靈感和底氣? 這幾年流傳著一句順口溜叫"防火防盜防記者"。這個"防記者"當然是防搞輿論監督的記者(對於吹喇叭抬轎子當跟班的記者,他們不僅不防,或電話"召記",領導未行祕書先通知新聞單位派人,或高價拉請,提供吃喝玩樂一條龍服務,"誘以官、祿、德"的花樣不一而足)。"防"的手段有多種。首先是牢牢控制本地的新聞傳媒,嚴令傳媒老總這個不準報導那個不準披露,違者即摘掉烏紗帽或砸他的飯碗;對於上級和中央傳媒的記者,則授意本地有關人員不得接受採訪,有的地方甚至由政法委另外專門制了記者證,只認他們這個證,不信國家新聞出版署制發的證。文明的設防手段是封鎖現場和消息來源,不文明的就乾脆採用暴力驅趕毆打記者,搶奪記者拍攝的音像資料。當然,威脅受訪的羣衆也是其中一招。記者的人身安全越來越沒有保障:揭發山西運城地區領導製造虛假的節水滲灌工程的記者高勤榮身陷囹圄;爲主持正義曝光海南一起賣淫嫖娼案的記者劉洪以被逼瘋;重慶女記者羅俠在採訪現場被人打成重傷……一起接一起傷害記者案令人髮指,也令從事輿論監督的人心寒。如果還是說"新聞記者是條狗",則毫不誇張地講,從事輿論監督的記者在某些官員眼中是威脅他們官運的惡狗、野狗,無人保護的記者則很像一條條喪家狗。CCTV的記者在《偷拍實錄》一書的後記中寫道:"很'牛'的中央電視臺記者,帶著偷竊般的心態,忍著內心的憤怒,以一名弱小平民百姓的身份,目擊著欺騙、凌辱、威脅、謾罵、違法、亂紀等一系列'精彩表演',這是中國新聞史上很特殊的一種現象。" 之所以如此,不需要多少理論水平和政治智慧,誰都知道,這是如今中國的新聞記者缺乏法律保護的必然結果。當事人不希望自己的醜事變醜聞,當官的要維護他們的所謂政績和政治形象,至少是避免因千夫所指而下臺,這都是人之常情。奇怪的倒是,我們天天在喊"依法治國",爲什麼就是遲遲不肯出臺"新聞法"或"輿論監督法"? "新聞法"已經呼喚有年,10多年來幾乎每年兩會期間都有提案提出。問題洞若觀火,大家都是明白人。據《中國青年報》2001年11月9日報導:"全國人大新聞局副局長沈掌榮對過去幾年中發生的嚴重侵犯記者人身權、採訪權的惡性事件記憶猶新。他特別提到福州記者顧偉因採訪老虎機賭博事件,被打黑槍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