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慮到毛澤東是偉大領袖的同時還是偉大的謀略家這一事實[1],很難斷言他那時究竟是確實不知道光明日報由誰人主編,還是明知故問。因爲,第一,光明日報向來就不曾由非共產黨人士編過,後離任的前兩屆主編胡愈之與邵宗漢,都是身份不常而不是從未公開的CP;第二,早在9個月前,在他《論十大關係》講話之後,中宣部就已經在緊鑼密鼓地活動着,爲光明日報物色總編輯。在這個講話裏,毛澤東已經預見到一年後的局面:
現在我們國內是民主黨派林立,其中有些人對我們還有很多意見。……形式上沒有反對派,所有民主黨派都接受共產黨的領導,但是實際上,這些民主黨派中的一些人就是反對派,在外交、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等問題上,他們都是又反對又不反對。……共產黨和民主黨派關係要改善。我們要讓民主黨派人士,談出自己的意見,只要說得有理,不管誰說的,我們都接受。
要說話,總得有塊地盤(大衆傳播媒介)。那時還沒有《世界經濟導報》,也沒有《現代人報》,不知誰首先想到了光明日報[2],而且是非共產黨員辦的光明日報,於是開始物色主角。本來;第四屆總編輯的第一人選是徐鑄成。當時,這位倔脾氣的老報人正經歷着他那份緣抗日而創刊的文匯報的第三次停刊;第一次是在1939年,被日僞停掉的;第二次是1946年,國民黨停的,這在前一節已經說到;第三次停在柯慶施手裏,時間是1955年,公諸於世的名義是「自動」。
1956年夏,徐鑄成正帶着他文匯報的原班人馬,北上首都,在與柳湜、葉聖陶(這兩位是當時的教育部長)和諧的合作中,輕輕鬆鬆地編着一張週二報紙《教師報》。姚溱找到他。
「喂,心情怎麼樣?」這位當年的宣傳部副部長問。 「很好,很愜意。你瞧,住在鄉下,有一部小車,沒事就到處玩玩。」 「嘿,昧心之論!你這人一輩子辦報,現在一週兩張的專業報紙,你過得了癮、安得了心?」 「的確安心。既然說了是社會主義改造的需要,文匯報停就停吧。現在教師報對我不錯,就安心在這裏做了。」
姚溱不再與他打迂迴,單刀直入解釋形勢:光明日報決定完全交給民主黨派,章伯鈞仍任社長,常芝青撤離,中央的意思叫他接任總編輯。面對這足夠誠懇的交底,徐鑄成也以實言相告:
「做事總要有一個班底,不能一人唱獨腳戲。現在我的人馬都在教師報,讓我光身一人去上任,這臺戲唱不了。」一再謝絕。 「好,那就不勉強了。」姚溱說。
徐鑄成拒絕了,中宣部開始進行第二人選方案。這次是喬木出馬,親自登門徵求儲安平的意見。
雖然又同齡又是小同鄉,與他這位被封過三次的同行比,儲安平是「嫩」多了。英國派頭的他不認「班底」說,也不以「上無常操」,或者「上下一日百戰」爲然,那是上百、上千年前的事了,那時候有政協嗎?有憲法嗎?他只認Fairy Play。他不用拉攏誰,也不用提防誰,包括,比如說,常芝青。後面我們將會看到,這種天真,令人心惻。
在談話中,喬木特別提到《觀察》,提到他成功地編這本刊物的時候,聯繫的一大批知識分子,希望將來主持光明日報,與這批舊朋友還要多聯絡,鼓勵大家多寫文章、多說話。喬木接着還特別補充說,過去工作上的助手也可以考慮邀些來幫忙。
雖然出自Prf.Laschi之門,安平畢竟是中國人。他潛在的虛榮心、他對「三顧茅廬」之恩德的顧念,再加上他1949年之後實質上的不得志,都決定了他的欣然受命。喬木接着的作法也是頗具人情味的,先安排他到青島去度蜜月(此時正值他鰥居10年之後的第二次新婚):
「把新疆的採訪寫完,上任的事以後再說。」喬木親切囑咐。
他去了,並在海濱寫作,直到秋天。1956年11月,他收到章伯鈞的信,稱經「各民主黨派公推」,請他出任光報總編。他於是也一本正經地復了信,表示接受。今天可以肯定的是,這「公推」顯然不過走走形式而已——中國八大民主黨派近40年曆史,類似的形式不知走了多少——但這次,應該說,「策劃」與「走」的雙方,都沒有絲毫惡意,雖然這已成的局面並不是人人都滿意的——這點,儲安平當時就有了察覺:
我當時有這樣一個感覺,章伯鈞並不歡迎我作光明日報的總編輯,他對我的態度是很冷淡的,我和他過去太沒有私人淵源,而黨的推薦我出任光明日報總編輯,他也不好拒絕。
讀者在這裏可將儲與胡、章二人的親疏作一個比較。遺憾的是,在後來的鬥爭中,他主要罪名之一竟成了「向黨猖狂進攻的章羅聯盟骨幹分子」。
1957年初,按照喬木「聯絡老朋友」的指示,他去了一趟上海。從他後來所作的交待看,一到上海,就去拜望徐鑄成。
當時,文匯報奉中宣部之命復刊已近半年,那場著名的關於電影的爭論,正鬧得火熱。當時,宣傳工作會議雖然還未召開,「雙百」的提法已經傳下來。徐鑄成很興奮,但也有不少疑慮。兩名小同鄉都不再提10年前之嫌,反覆切磋這8個字的含義。此時正主持着一張報的徐鑄成處處顯得比較保守,而即將接手另一份大報的儲則「冒」得多了。他不同意「爭鳴」只限於學術界,覺得應該擴展到政治領域,鼓勵大家多講話。他斷言:「百家爭鳴是全面的,電影討論只是一個局部。如果電影都不能談,還談什麼百家爭鳴?」
讀者在前面已經知道儲安平辦觀察的勁頭,對他在此刻所作如是說定覺毫不足奇。有趣的是直到30年後,在1986年一次軟科學的閉幕式上,當一位開明的中共高級幹部將此觀點再度明確提出時,與會羣衆竟欣喜若狂,於是引出鄭重的否定與又一次的再否定,直到今天尚未了局。
當時,儲氏新的出任已在上海傳開,原光華同學決定聚會作東請他。據趙家璧回憶:晚飯約在7:00,大家左等右等,等到9:00這位老學友才匆匆趕到。坐定之後,沒吃幾樣菜,就被一部小車接走了——其紅火與煞有介事至此。
幾乎與此同時,在1957年那乍暖還寒的季節,毛澤東爲說服黨內接受「雙百」的「親蒞巡說」,也正在緊張運行中……
先是在9省市宣傳、文教部長座談會上,而且開宗明義就談到今天誰都不大敢碰的「言論自由」:
有選舉權的,憲法就規定他有言論自由,我們就得讓人家講話。我可以批評他,他也可以批評我,這就是言論自由。有人間馬克思主義可不可以批評?如果馬克思主義被批評得倒,也該倒,證明那樣的馬克思主義是沒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現在不是放多了,是少了,應該再放。
接着和文藝界人士談話。當時有一種風氣,一篇文章的好壞,不看文章本身,只看「上頭」對這篇東西的態度。在那次會上,大家很想摸摸主席對陳其通等四小「左」的態度。毛澤東的反應乾脆利落:
說我說陳其通四人的文章是好的,真奇怪,我說是要放的麼!
當時顯得最爲開明的康生立刻爲這句話作注:「這是他們對『雙百』政策有懷疑。陳其通等人的文章正適合他們的胃口。」
在與新聞出版界談過話之後,又會見高等院校校長,開場第一句話即爲:馬列主義從來就是主張百家爭鳴的。
這位巡說人接着去了天津,這次是對黨員幹部:
對百家爭鳴沒有信心,對百花齊放怕放出毒來。我看完全不是這樣。若採取壓服的辦法,不讓百家爭鳴百花齊放,那就會使我們的民族不活潑、簡單化、不講理;使我們的黨不去研究說理、不去學會說理。至於馬克思主義可不可以批評,人民政府可不可以批評,共產黨可不可以批評,老幹部可不可以批評,我看沒一樣不可以批評的,只要誰願意批評。什麼人怕批評呢?就是蔣介石那樣的黨,蔣介石那樣的法西斯主義。
三天之後,老人家又到了上海。這裏有他的好學生柯慶施。而且下面這番話,就是在柯慶施主持的會上講的:
同知識分子問題、科學藝術問題有密切的聯繫的,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個方針的問題。關於這個方針,我們還需要在黨內作許多宣傳解釋工作。有些同志覺得這個方針太危險了。百花齊放,放出些鬼來怎麼辦?關於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有人說,「民主黨派有什麼資格和我們長期共存?還是短期共存吧!」「我監督你,我還用你監督呀?你民主黨派哪年打的天下?」所有這些意見都是反對我主張收。中央認爲主張收的意見是不對的。……不但在純粹的科學藝術的問題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問題上,只要不屬於反革命一類,也應該讓他們自由說話。
接下去到了南京,會見南京部隊、江蘇安徽兩省的黨員幹部。此時毛澤東自己也承認「我變成了一個遊說先生,一路來到處講一點話。」
沒有誰能否認,在這一連串的會晤中,毛澤東雄才大略、博聞強記、風趣幽默的特點發揮到了極致。至於與會的大多數,如果不看他們畢恭畢敬的迎送,不聽他們當時報以的掌聲,僅從他們四個月之後的作爲來反觀,當時多半隻有跟着傻聽傻樂的份。
與這輕鬆融洽的氣氛相對照,對人民日報的批評顯得分外嚴厲。除了上文所引「死人辦報」外,還有:
宣傳會議未登消息是個錯誤。這次宣傳會議黨內外人士合開的,爲什麼不登消息?最高國務會議爲什麼不發社論?爲什麼把黨的政策祕密起來?這裏有鬼。鬼在什麼地方?……省委書記會上爲什麼聽錯了?這叫「各取所需」。最近黨的政策的宣傳,人民日報不是沒有抓緊,而是沒有抓……你們多半是對中央的方針唱反調,是牴觸的,反對中央的方針的,不贊成中央的方針的。……中央開了很多會議,你們參加了,不寫,只是使板凳增加了折舊費。如果繼續這樣,你們就不必來開會了,誰寫文章叫誰來參加會。
在這一陣緊似一陣的批評中,毛澤東提到了光明日報:
對當前政治情況的討論,光明日報連發了幾篇,都是當前重要的政治情況(如「爲放而拿」),這些情況編輯部應該討論。
這裏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徐鑄成朝見毛澤東時的那番景象,也就是本章開頭所說的那次會見。這次沒有儲安平,但常芝青與鄧拓都在場,顯得特別受冷落。那次會見,徐鑄成遲到了。他後來回憶當時的情景:
聽到康生的介紹,老人家立即伸出大手,緊緊地握着我的手說:「你就是徐鑄成同志?你們文匯報辦得好,琴棋書畫、梅蘭竹菊、花烏蟲魚應有盡有,真是放得好!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們的報看,然後看人民日報,有功夫再翻翻別的報紙。」
當時徐鑄成正被上海市委「反擊」得心灰意冷,聽到主席的這番讚賞,「我心中翻起熱流,感到無比溫暖幸福。」
這時康生宣佈,有什麼問題要主席回答的,請提出來。
徐鑄成趕緊揣出他心中最大的結:「宣傳雙百,心中無數,抓緊一點還是松一點,該怎樣掌握,請主席指示。」
讀者此刻應該注意的是,毛澤東曾經考慮到「鳴放」的高度和深度,徐鑄成此時根本沒有觸及,更不必說提出諸如民衆對權力機關的監督與批評等等了。他只是向黨中央主席請教,如何更好地宣傳中共的方針。
毛澤東沒有正面回答,只講了一番片面性的問題。在說到魯迅、李希凡、王蒙等人都有片面性之後,突然說了一句:「我看姚文元片面性比較少。」那時姚是上海市委宣傳部文藝處的一名幹事,在座的幾乎沒有人知道他。但這位小姚不但被特別指定到北京參加會議,還受到這樣的當衆稱讚,足見毛澤東要培養自己得心應手的理論家的心願在那時就埋下了。歷史已經證明,姚的文字果然在後來的每個關鍵時刻,都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徐捨不得放過機會,仍舊追問:「我體會雙百方針的提出,在政治思想上說,是徵求高價的批評,讓人民暢所欲言,說的不對慢慢再說清楚,不要一下子壓下去?」他在這裏並不敢強調嚴正的批評(如馬寅初的「人口說」)對黨對國之寶貴,只問說錯了能不能不壓,而且限定了政治思想領域。
毛主席回答道:「你的意見很對、很好。」
徐依舊不放心,舉出因電影討論而遭圍攻的實例,追問:「請問主席,這時我們應該怎麼應付?」
徐鑄成不愧老資格報人。他的這個問題之足夠咄咄逼人,不在語氣,而在回答者無法用含混的語言大而化之。毛澤東當然不會被問住,他在幾乎不能迴避的時候還是避開了:
「我叫周揚同志給你們這場討論寫一篇小結,批評及反批評的小結,這就叫正、反、合,這就叫辯證法嘛,你同意不同意?」面對如此玄妙、又如此高屋建瓴的答案,徐鑄成還能說什麼呢?他於是點頭稱是:「主席想得很周到,我完全同意。」
在這次接見中,毛澤東預告了共產黨的整風:「要用小小民主的方法,就是小民主上再加一個小字,就是毛毛雨下個不停,先整共產黨。現在我們有些同志裝腔作勢,他們沒有本錢,又要做官,不擺架子就不行。」
毛澤東下面的一番話很難不令人感動。他誠懇地交底,說他的思路:「我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談話,本來在心裏積累了很久,去年已經講了幾次,後來又看了些事情,看了陳、馬他們的文章,想到會有人以爲他們的文章是代表中央的意見,因此覺得有好好說說的必要。」他承認共產黨的拿手好戲是打仗、專政,「說到辦報,共產黨不如黨外人士,全國性辦報沒有經驗,辦學、搞出版、科研都是這樣,現在是外行領導內行。」他並且囑咐:「開會的時候,就是要黨內黨外的人在一起,共產黨不要關起門來開會。」這不可能不給人以黨內黨外不分彼此親如一家的印象。
4月30日,毛澤東落下了他這場偉大的戰略佈署中最後的也是最濃重的一筆。
那是「五·一」節前夕,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親自約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請大家幫助黨整風。他說:「現在是新時代和新任務,階級鬥爭結束,向自然宣戰。」他還着重號召民主人士揭露教育、衛生等部門的官僚主義,並責成專人就民主人士的有職有權和學校黨委制問題專門開會徵求意見。
這次時間地點選得可謂匠心獨具:春天已經到了,第二天就要過節,伴着巨大的紅燈籠,被告知以「階級鬥爭結束」:想來也只有在這樣的氣氛中,毛主席才會親切地使用這樣的字眼——這字眼後來傳到我們主人公耳中,又從他口裏說出來,成了十惡不赦、萬劫不復的罪行:
「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希望對老和尚也提些意見。」
「五·一」節之後,再未見毛澤東出來。用今天的眼光看,頗似臨戰前短暫的寂靜。
※※※※※
1957年4月1日,儲安平正式上任。完成這一形式的,正是對他「不好拒絕」的章伯鈞。請看他自己的回憶:
上午9:00,章陪我去了光明日報,到了報社,各部主任都在歡迎我們。章伯鈞說:「我把儲安平同志帶來了,他是一個作家,增加了光明日報很大的力量。」停了兩三分鐘,他又和別人閒聊了幾句,坐了五六分鐘,他就先走了。
接着當然是新任總編致辭。儲安平此時拋卻了1946年辦《觀察》時的作派,不再強調自由、民主、進步、理性。他開場的一番話至今光明日報的老職工都記得:
「我到這裏來工作,李維漢部長支持我,黨是我的後臺。」他們還記得,在後來的編輯部大會上,他也一再重申:「李維漢部長曾對周揚部長說,以後若是有人批評儲安平先生,你要爲他撐腰。」
他開始上班了。那時,共產黨支部在光明日報的活動是地下的,組織生活總是在下班後進行,而且是在常芝青家。但民盟的組織生活在報社內完全公開。4月9日,儲安平回孃家一般地參加了民盟支部的組織生活,還發表了講話:
4月1日來時,心情很平靜而從容。和大家相處如家人感覺。爲什麼?是否胸有成竹?是否有大政方針?是否拉了多少稿?是否摸了底?我卻什麼也沒有。只准備和大家商量。受黨的教育要表現在行動中,並需以誠意待人,向人學習。
在講了對這張即將接手的報紙的印象之後,他又說了一番其實不該在這種場合說的話,後來都成了揪住他打個不停的辮子。不能說他對這種「受命於非常時刻」之兇險沒有一點思想準備,但對兇險將來自何處顯然估計錯了地方:
我有信心,但不可能無困難,這是規律。民主黨派多,一定要捱罵。我們要估計到這些困難,做得盡力,罵也不怕。辦報就在風浪之中。是否符合事實,風浪也不怕,要登。要精神,要沉得住氣。
接着,他開始一一拜望各民主黨派的宣傳部長和大學裏的著名教授。前者屬於例行公務,如民進的馮賓符,農工的嚴信民,民盟的羅隆基、薩空了,民革的王崑崙等等。後者當然都是一些聲氣相通者,包括數十年舊遊:袁翰青、金克木、楊人楩、費孝通、錢偉長、彭子岡、王恆守等等。這些人後來當然也一個不漏地同時被激發起來,又同時遭到反擊。就在這前後,他開始與編輯部的同人交談——在不到三週的時間內,他「見了94位同志,其中26位是個別談的」。雖然這在後來也成了罪行:「施展卑鄙伎倆,企圖從社會主義接班人的這個環節上來拉攏、收買青年,篡奪黨的領導,爲他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準備着後備力量」,不過,這種幹勁,在光報創始至今的十多位總編輯中是絕無僅有的——當然,這也有說道,「反革命熱情高漲」云云。漢語的遣詞與思維邏輯到了這個份上,真該是「無聲勝有聲」了。
當時,常芝青還未撤出,作爲原任,儲安平對他起碼在表面是很尊重的。比如第一次向社長章伯鈞彙報工作,就是在與常及總編室主任高天充分商量並取得一致意見之後。但此時他一定感到當初勇氣十足的單槍匹馬上任是有些唐突了。這感覺可能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在毛主席共產黨這種宏大的氣勢面前,他的班子有點力不從心,用他自己的話說——這也是他後來最大的罪狀之一——「當前最大的問題是(黨)鼓勵大家鳴放,而光明日報在鳴放的報道上落在後面,」費孝通當時是這樣描述他的:「很起勁,把光明日報看成他辦的企業」。
他開始拉人。首先盯住的當然是大公報,他就商於常芝青,能否在保證光明日報領導層有4名共產黨員的前提下,請王芸生在這要緊的時刻幫一把。然後是親自出動拉人,爲光報拉有學問、有能力、有影響,還要有色彩的人。最先盯上的是潘光旦與費孝通——他這時肯定已經完全忘掉費先生50年代初在他的復刊的《觀察》上發的那一串既無學問也無色彩,而且自己決不會將其選入文集的那些準垃圾,他更看重他真正的人,而不是作給人看的人。他向他們交待政策——「政策」是儲安平之流說了算的麼?這實在滑稽,也實在堪憐——拉稿,責備費先生不該把《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那樣的好稿給了人民而不給光明。他計劃給費專闢一個專欄,甚至要將費調到光明日報社,已到問費一個月拿多少薪水的程度。
他深感光明日報缺乏筆政人才,羅隆基向他推薦陳新桂,說這是民盟總部幹部中理論水平比較高的一位。儲進一步打問此人爲人作風如何,是不是容易共事。羅隆基說:「這一點要說清楚,陳這個人很直爽,有話就當面說,不顧別人的面子下得了臺下不了臺。」這種特色(或稱缺點)儲安平絕對不在乎的,但章伯鈞不同意,只得作罷。後來事態發展證明,陳新桂確是一名幹才。他的言論與態度,僅從57年暮春的版面上看,如果不是最突出,也僅次於章乃器。反擊時那些常用的詞對他都失去了效用,只好給他套上一頂無可無不可的帽子「荒謬絕倫」。
他還曾與章伯鈞多次權衡,能不能在社委會之下設個常委會,要麼多設幾名副社長?他還想成立社委會的顧問團和編輯部顧問組……儘管時刻想着「分寸」,想着各種勢力的協調——這實在夠累人的,而我們中國人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這上面了——他的急切與一計不成又生一計,簡直到了不避嫌的程度。不幸的是(或者說,幸運的是),他的這些想頭,沒有一個兌現,包括他帶着幾乎孩童般的快樂執意要發表的錢偉長夫人與周培源夫人推薦來的一篇小品文《公開徵求拼音專家,請將左文譯成拼音文字》[3]。儲安平直到辭職的時候,還是單槍匹馬一人。
5月7日,在向章社長作了全面彙報的基礎上,他第一次在編輯部全體大會上公開他的改進報紙工作的幾點意見。
首先,他提出在新的政治形式下要更進一步把光明日報辦成名副其實的民主黨派報紙。
怎麼辦?他提出雙軌。一方面團結、組織和聯繫全社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另一方面努力反映民主黨派成員的意見和要求。他認爲,「光明日報應該成爲民主黨派和高級知識分子的講壇,要創造條件主動組織推動他們對共產黨發言,從政治上進行監督」。佈置要聞部的工作時,他要求他們多「搞人民生活(物價等)問題的報道,要主動去發掘,體現政治監督,代表普通百姓講話」。或許是在與高級編輯人員談心時,他曾發表過「報紙與黨和政府存在着根本矛盾,那就是報紙要登,黨和政府不許登」一類評述。可以認爲有所指,也可以認爲是一般議論,到後來都被原封揭發出來,令與會者個個義憤填膺。
對他的辦報方針的批判是嚴厲的,已沒有絲毫可迴護的餘地:全盤否定黨的領導下的成就,懷着重大陰謀,實踐一套完整的、反動的資產階級辦報路線。至於雙軌,那完全是騙人的鬼話,他要搞的當然是單軌,是脫離了社會主義軌道的另一條軌道。
應該說,儲安平提出的種種方針,不會是他信口開河,老實講也沒有多麼了不起的獨創性,其內核,主要來自中共中央統戰部在4月裏召開的第七次工作會議、在這個會上,李維漢明確提出,「貫徹『放』的方針,鼓勵黨外人士唱對臺戲」——後來這一精神衍化爲讓光明日報與人民日報唱對臺戲。李維漢做人一生唯謹,很難想象這種字眼會由他首創。遍查文獻,終於找到統戰部一位副部長說過,這種嚴肅又戲諺的話,還是出自毛澤東。但李維漢的態度是明朗而堅決的,他堅信「對民主黨派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是一個根本性的安排。各民主黨派在憲法賦與的權利義務範圍之內,享有組織獨立、政治自由和法律面前平等的地位,不僅是黨的政策要求,而且是憲法賦與的權利。」而且,作爲一種信條——如果不說是策略的話——從理論上講,他也並沒有改過口。不僅在1957年4月間如此,就是到了夏、秋,乃至到了他口授自己的回憶錄的80年代中,也是如此。不幸因爲漢語的無比豐富以及多義性,上面的一段話,在不同的局面下,是完全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釋的。
接手光報,儲安平最拿不出辦法的恰恰是他最看重的社論;對此,他曾向各民主黨派宣傳部門徹底交底:
就現在情況來看寫社論是比較困難的。因爲,光明日報過去的社論,一種是數條,四平八穩;再一種是說共產黨的好話,歌功頌德。批評監督的社論沒有,要寫批評監督的社論,必須社務委員會支持。光明日報的婆婆多,八個民主黨派是八個婆婆,民主黨派有幾百個中央委員,是幾百個婆婆,一個婆婆一個看法,就很困難。因此,必須社委會授權。在沒有授權之前,只能用個人名義寫這方面的文章。
此外,對於始自延安新華日報改版,而降至1957年甚至降至今日都不憚其迂的「問題寫作」,也成了他「改進」的目標之一。對於報紙通過「搞問題」而指導工作,他並不是不知道,但他認爲:「在目前,這種情況已有所不同。特別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提出之後,鼓勵大家獨立思考,對報紙指導工作的要求已經減少了。」他對報紙的理解是:「我們的目的在揭露,分析和解決問題,是共產黨的事。」對於重大問題要不要向中共中央宣傳部請示,他的底氣似乎太足了點:「我們是民主黨派的報紙,用不着!」
那麼,他此刻是不是不再認爲「(共產)黨是我的後臺」了呢?應該說並不是。筆者甚至傾向於認爲,自1949年至今,很少有誰的言行不認爲「黨是我的後臺」吠比如讀者諸君正在讀着的這篇文章的寫作與發表,就是「黨是後臺」的直接結果。問題黨不是一個人;就算是一個人,也不是一個死了的人;就算是死了的人,也總有不止一篇白紙黑字的文章留在世上。儲安平太相信黨對他作爲一個囫圇個的、有思維與創造能力的活人來相信的程度了,更忘記有人或許還會想到他的祖父,他的師傅,還有他在國民黨裏的私人朋友。以此來對儲安平的智力水準下判斷是不公正的。他太着迷了,迷到犯傻的程度。
或許並不是這樣,他其實已經把所有的一切都考慮進去了。但他答應下來的既然是「做事」而不是「做官」,就顧不得那許多了。而且,就在他主持光報的短短70天中,這種情緒也沒打算隱瞞,幾乎所有的人都記得他說的那番頗帶了一點感情的話:
光明日報讓民主黨派獨立自主地辦,這句話說得好。但我要看看究竟怎麼樣,看看我到什麼地方就要受到阻力不能前進。我要碰。我要扛一扛風浪,擔一擔斤兩。我要看碰上多少暗礁。
共產黨向全社會正式通告自己的整風,是在5月1日,即毛澤東天安門城樓座談會的第二天。也正是從這一天起,被偉大領袖和中共的誠意所感動,覺得再沉默就太大大對不起黨的「民主黨派、知識分子、資本家、青年學生」,包括他們之中的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們,開始正式鳴放。
頭幾天,大家不怎麼想動;或者說,還不知該怎麼動;要是對中華文明的路數比較熟悉,就知道,這是大夥正不約而同地按照中國的老例,先看看再說。真正着急上火的,只有那些自以爲對幫助黨整風負有重責的人,如儲安平、欽本立等。爲發動鳴放,或者換句話說,爲了「把報紙引向資產階級方向」,他們真是煞費苦心。儲安平「最惡毒的」九大城市座談會的主意,就是在這絕境中逼出來的。
到了5月6日,中共中央統戰部開始召集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開座談會,各部門、各省市和各高校,也都檔次遞降地依樣召開,請大家幫助黨整風。一開始;當然還是啓發,鼓勵;漸漸地,有人發言了;漸漸地,發言愈加尖銳起來;文匯報、光明日報等則把其中最「精彩」的送上版面。雖然後來儲安平遭到衆口一詞的指斥,說什麼「惡毒」他登什麼。這實在有點冤枉他了。他只是追求言論自由,追求不受限制地表達這一原則。某些重要的反駁意見,如馬寅初認爲「高小吠應該設黨委,沒有黨委書記我這個校長沒辦法做」這類言論,他都照登。
今天的讀者大約只知1957年有右派卻不大知道他們怎麼個「右」法。擇其要而述之:
1.黨委治校抑或校委會(教授)治校(黃藥眠); 2.共產黨內的宗派主義作風(章乃器); 3.民主黨派參加協商應有名有實(羅隆基); 4.文教界共產黨員負責人不稱職[4](陳銘樞); 5.共產黨以黨代政,黨不應該直接向人民發號施令(黃紹竑);黨政不分,中央是根(楊玉清) 6.共產黨員的特權思想(李伯球);黨員特權造成黨與非黨之間的牆與溝(龍雲、張雲川); 7.人民代表大會與政協制度需要改造(葉篤義); 8.三大主義(官僚、教條、宗派)限制新聞自由(張友鸞); 9.要求人生三大事:物質生活保障、精神的民主與自由(章伯鈞); 10.政協、人大、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應是政治設計院(章伯鈞——這話最初是毛澤東講的); 11.羣衆鳴放得越徹底,黨的威信就越高,把鳴放重點放到基層去(王造時); 12.成立平反委員會(羅隆基——他作此語的出發點是懷疑現有的黨政機構自我改善的能力); 13.胡風不是反革命分子(北京大學學生); 14.依據馬克思主義理論來套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榮子正); 15.我們對當前經濟科學的意見。這是陳振漢等六位經濟學教授特地聚在一起認真討論之後準備上呈的,事後對他們進行的概括性批判爲:「會上六人都發表了意見,污衊當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教條主義、國家經濟工作中有很大的缺點錯誤卻不準公開討論。企圖用資產階級觀點來指導國家的經濟建設,說政府應該吸取資產階級經濟學說來制定政策,制定經濟政策時應請經濟學家參加設計,政策制定後應公開討論監督。」(陳振漢、徐毓楠等) 16.共產黨不要不相信我們知識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羣衆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推翻你們。羣衆不敢信任共產黨,因爲他們在八年中體會到共產黨善變。若你們再不爭氣,腐化下去,那必走這條路,總有那麼一天了。這不能說不愛國,因爲不要共產黨領導,大家也不會賣國(葛佩琦——這就是後來被概括的「要殺共產黨」的那段話的原版); 17.官僚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危險的敵人。定息不是剝削。(章乃器); 18.黨天下:向毛主席周總理提些意見(儲安平); ……
儲安平的這個發言是在6月1日作的,差不多是統戰部座談會閉幕的前夕了。儲安平自己交待:
解放以後,一般說來,我很少在外面說話。鳴放開展以後,也很少講話。九三、作家協會來邀,都未發言,多少採取逃避的態度。一則我對發言的積極性不高,二則我也沒有什麼具體的問題要談。所以統戰部座談會開得很久,我一直沒有去。5月30日上午統戰部來電話要我去。我答應去,但說明不發言。下午聽說6月1日還要開會,統戰部彭處長希望我6月1日發一次言。我31日上午還在報社工作,31日下午在家寫發言稿,那天下午和晚上一直在家,沒有外出。伯鈞同志說我的發言稿羅隆基看過,並無此事。
儘管儲安平是一個風頭很健的人,筆者依舊傾向於相信他確實直到5月31日還不想到會上去說話——這當然並不意味着他無話可說。但當一頂頂高帽送到頭上,一聲聲懇摯的要求送進耳廓,他讓步了。而他一旦決定講,就想博個滿堂彩。用後來章伯鈞的評價,就是「現行政治上的一些人,大都只說些雞毛蒜皮的事情,要汽車、幹部、房子之類,能談大問題的人不多。」
在那天的會上,他不但持有照本宣讀的發言稿,這稿還是打印好、估算好版面,並特別注有「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發言稿」,「希用原題、原文勿刪」字樣的一份交報館直接發排的成稿。
他期待的效果出現了。會上即博得一片喝彩,會下更盛傳不衰。大家都記得馬寅初當時即用手拍着椅背,連稱Very good,Very good!第二天,在見報的同時,中央臺全文廣播。他以少有的親切對孩子們說,「來,聽聽,這是爸爸昨天在會上的發言。」他不知道的是,毛澤東親自起草的那篇給黨內幹部閱讀的文章《事情正在起變化》已發下半個月,此時正是文中早已點明的“現在�遺傻慕セ姑揮寫鐧蕉サ悖欽諦爍卟閃搖N頤腔掛盟遣褚桓鍪逼冢盟親叩蕉サ恪!?p> 頂點在哪兒呢?至今未見任何權威性的文獻加以說明。若將隨後批判的火力的強弱,及對人頭處理的寬嚴作參考,高潮應是那個與治蝗蟲的農藥同名的「六六六」事件了,即6位教授在6月6日應章伯鈞之邀緊急聚會,討論鳴放形勢。對照他們當時所懷有的悃誠,和後來對他們的解釋,只能說,「足令歷史帶淚看」。章伯鈞先介紹學校的局面,請大家研究民盟在運動中應該如何工作。費孝通說,現在各大學的學生情緒激烈,情況十分嚴重。老師若去給學生領頭,事情就鬧大了。黨在羣衆中的威信就完了。曾昭倫認爲形勢一觸即發,共產黨大意不得。錢偉長特別指出學生在到處找領袖,期望着教授們站出來說話……他們決定這時候一定得出來,不能讓共產黨進退不得,要幫助真正繼承了列寧衣鉢的「毛公」,要幫助共產黨穩住局面。
此時,距《人民日報》那篇晴空驚雷般的社論《這是爲什麼》的發表只有2天……他們怎麼會料到,毛澤東對「六六六」的理解竟是這樣:反動的階級敵人爲什麼自投羅網呢?他們是反動的社會集團,利令智昏,把無產階級的絕對優勢,看成了絕對劣勢。到處點火可以煽動工農,學生的大字報便於接管學校,大鳴大放,一觸即發,天下頃刻大亂,共產黨馬上完蛋,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鈞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的目前形勢的估計。這不是利令智昏嗎?李維漢去世前的一段回憶,或許可以部分解釋這一局面形成的過程:
在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座談會開始時,毛澤東同志並沒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爲了反右而開這個會,不是「引蛇出洞」,兩個座談會反映出來的意見,我都及時向中央常委彙報。五月中旬,彙報第三次或第四次時,已經放出一些不好的東西,什麼「輪流坐莊」、「海德公園」等謬論都出來了。毛澤東同志警覺性很高,說他們這樣搞,將來會整到他們自己頭上,決定把會上發出來的言論在《人民日報》發表;並且指示:要硬着頭皮聽,不要反駁,讓他們放。在這次彙報之後,我才開始有反右的思想準備。那時,蔣南翔同志對北大、清華有人主張「海德公園」受不住,毛澤東同志要彭真同志給蔣打招呼,要他硬着頭皮聽。當我彙報到有位高級民主人士說黨外有些人對共產黨的尖銳批評是「姑嫂吵架」時,毛澤東同志說:不對,這不是姑嫂,是敵我。
在這場較量中,很值得共產黨驕傲的,是那段幾乎每個中國人在「文化革命」中都背得滾瓜爛熟的語錄——「陽謀」;
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爲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只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他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階級敵人是一定要尋找機會表現他們自己的,他們對於亡國、共產是不甘心的。不管共產黨怎樣事先警告,把根本戰略方針公開告訴自己的敵人,敵人還要進攻的。
這確是事實。毛澤東的警告在1957年1月即已作出:
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種怪議論,不要共產黨呀,共產黨領導不了他呀,社會主義不好呀,如此等等,是不是想復辟?
但怎麼解釋4月30日天安門城樓上的座談會呢?怎麼解釋那幾乎征服了所有文化人的談笑呢?從4月30日到5月15日,只有半個月,究竟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或者不過什麼觸動,使他一下子暴躁起來,而釀成這半個世紀都未必緩得過勁來的悲劇呢?
李維漢這樣回憶在5月10日前後「向主席彙報」的情景:
……及至聽到羅隆基說現在是馬列主義的小知識分子領導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外行領導內行之後,就在5月15日寫出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文章,……表明毛澤東同志已經下定反擊右派的決心�?p> 怎麼估計羅隆基這幾句話對毛澤東的傷害也不過分。這傷害不僅僅在於諸如誰打天下、誰坐天下,交椅怎麼擺等等要命的問題,而在於它是一箇舊傷疤,傷害一直可以追溯到1910年末,追溯到他在北京大學當圖書管理員的時候[5]。更不可以忽略的是,這傷害也不是一人一時所能加予的,張國燾、羅章龍、王明、張聞天,也許還有別的人,總之,一批受過高等教育或者洋教育的人,沒準都讓他十分不舒服過,特別在他們還沒領教他的手段而「放肆得很」的時候。當然,當他們在他的智慧下活動的時候,他可以稱讚,甚至尊重他們;要是想反,他就要讓他們看看,究竟誰「大」,誰「小」;誰真有學問,誰「書讀得越多越蠢」。對這批衣冠楚楚,滿口洋文,愛洗澡、愛吃藥的秀才們隨意嘲弄,打趴下再拎起來,拎起來再打下去,可以說是偉大領袖終生樂此不疲的遊戲。
5月上、中旬,相當一批親隨已經窺知了毛澤東的意圖。黨內文章一下達,高級幹部們心裏都有了數。他們當中的一些人於是東施效顰,也殘忍地玩弄起那些「不可一世的高級知識分子」來。比如人民日報依舊在發社論:《繼續爭鳴,結合整風》;如不但統戰部的座談會仍舊開,新聞界等在16日之前還新召開了會議;如幾次三番催促儲安平之流發言;甚至擔心右派品種不齊,有意製造一些。請看李維漢的回憶:
工商座談會期間,有人提真正的資本家與會不多,代表性不夠,於是又不斷擴大規模,找了北京的吳金粹、天津的董少臣、上海的李康年等一些人到會鳴放,後來這些人都被劃爲右派。
但當時這批已知情的中共高幹確實有意保護一批人,究竟是有組織的佈置,還只是出於他們個人的友情,今天就不得而知了。今日學界盛傳的是,田家英——他是毛主席身邊的大祕書,「文化革命」剛剛開始就自殺了——特別着急,急得火燒火燎。一再提醒他30年代就認識相知的老友曾彥修,讓他快快閉嘴,不過曾彥修對此予以否認。他清楚記得的是,人民出版社的一些「過激鳴放」把他嚇壞了,比如「到人事科搶檔案」、「到天安門示威」等等。他覺得沒有辦法控制局面,只好就商于田家英,問能不能把他從這裏調開。田的回答是:「你膽子太小了,要放手發動羣衆,根本還沒有發動起來嘛!」他又去找當時文化部主管出版的副部長陳克寒,陳也說:「沒發動起來!真有什麼事也沒什麼不得了,怕什麼?!」曾彥修記得很清楚,這時確實已不是5月初而是5月底。曾彥修認爲,或許大家把田家英類似傳說中的另一次事先警告安到了他的頭上,那次是對張聞天;時間是在2年之後的廬山會議上。那次,田家英與胡喬木苦苦勸說張聞天不要發言,張還是發了,從容而坦蕩。當然,這已經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柯慶施此時心情可能相當複雜。他特別關照文匯報,凡是北京方面來的給人戴帽子的稿,都要事先與他通氣。那位老黃牛一般只知幹活、不善言詞的文匯老人嚴寶禮的名字就是北京點了而由柯慶施勾掉的。這一義舉,並不表明柯慶施對知識分子在中國的地位與作用有什麼與毛澤東不同的見解;如果非說有,也只在用語方面有了一點突破。他獨到的評價是:中國知識分子用兩個字就可以概括,一是懶,平時不肯自我檢查,還常常會翹尾巴;二是賤,
(http://renminbao.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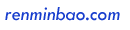











 打印機版
打印機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