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白条”如何出笼
一九八○年,人民公社正式瓦解,农村实施“包产到户”,农民(原来称公社社员)开始得到“松绑”,有一点耕作种植自主权,劳动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的同时,对党的农业政策依然疑虑重重,收获的粮、棉、油,大多储存在家里,不肯轻易卖给政府。所谓“家有粮,心不慌”,这是中国农民三千年来养成的传统心理。粮食是影响全局的最重要战略物资,为了稳住农村的大势,人口最多的四川和生活最穷的安徽两省的省委书记赵紫阳和万里,分别提出好几项顺应民心的重大改革政策,得到农民热烈拥护,成为十年文革浩劫后农民所能尝到的“定心丸”。因此,当时流传着“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佳话。
“以粮为纲”成次要国策
农村局势大致稳定了,社会主义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即将经济改革转向城市商贸,尤以“对外开放”摆在首位,号召“全民经商”,提出“让部份人先富起来”的诱人口号。这一下,穷极无望的中国人,好象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一切向“钱”看,一发不可收拾。广东沿海地区的乡镇干部,特别是毗邻港、澳地区的党政军警,无不争先恐后,引进“外资”,大做“无本生意”,正财与横财并发。万元户、十万元村、百万元乡、亿元县相继荣登富榜。
既然“对外开放”有大利可图,“以粮为纲”的农业,即被摆在次要的位置上,每年必备的粮食收购专用款,管理也逐渐松懈。许多财政偏紧甚至拮据的地方,挖“肚皮”补“脊背”,试着将购粮款的一小部份,挪作他用。于是,传统的“信用契约”——白条,就在新形势下兴起了。看着农民对白条虽不大接受,但也不敢不接受,各地政府就放胆大干。
“计划经济”加党的绝对领导,人力、物力、财力,绝大多数取自农村,农民除交公粮、卖余粮外,还要负担名目繁杂的“派款”,如水利、修路、教育、卫生以至葬丧费等等。
一九八五年以来,农业的所谓“改革”完全停顿,内地农民纷纷到东南沿海地区打工挣钱,形成了中国现代史上蔚为奇观的“民工潮”,人数超出一亿。这支庞大的“盲流”大军,只要有饭吃,有钱拿,什么脏、苦、累、贱的活都干。据说其中有一位从河南农村来的老太太,五十出头,身板还算硬朗,原是当地基层的党支部书记,党政人财一把抓的第一把手,却在广州街头拾破烂,挣钱吃饭。当地基层领导要她回去,依然当党支部书记,她死也不肯。她对人说:终年催耕催种,粮食登场了,公粮照交,余粮照卖,不见钞票,只给白条。再给乡亲们唱黑脸,怎么唱得下去?
白条背后的阴影
公社化时期,没有所谓打白条,但阴影早已存在,只不过是隐性,不经深入观察,不容易发现。因为那时的“派购任务”,都由“两级核算为基础”的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承担,加上公社一级的“统一调配”(实际上是吃大锅饭),政府所有的农业征收和收购,都不与农民个人直接发生关系,损害农民利益的这一阴影,被掩盖起来。包产到户以后,“派购任务”直接与农民发生关系,每年收购粮食的支付款,多达数千亿元,成为农业上最大的一笔支付款,也是农民赖以为生的最基本收入。政府规定以“官价”收购粮、棉、油及其它农副产品,农民的产品不能“随行就市”,无法分享“市场经济”的好处,打白条便成为农民的一场做不完的噩梦。
东南沿海地区,由于“经济特区”政策辐射力的影响,乡镇企业(即原来的农村公社、生产大队轻工、手工厂)发展很快。笔者于一九八七年在珠江三角洲访问,发现一家农村小厂,十多名中青年妇女,以一座破旧祠堂作场地,一架简陋人力印纸机,几十把剪刀,专门制作冥品,大至洋房汽车,小至鞋帽美钞,一箱一箱,经香港销往东南亚,每年赚外汇约达百万美元。女工仍然按工分计算报酬,所得无多,绝大部份利润归政府所有。
“打白条”是断绝农民生计的腐败
在这样有利可图的形势下,各地方政府无不争先恐后,制定名目繁多的优惠政策,向外招商。其中主要的一项,是提供廉价土地,由外商作商业用地。以广东为例,至一九九七年不完全统计,出卖出租农村土地总金额达万余亿元,其中胡涂账或不明去向的款项,达四千多亿元。打白条是近二十年来无法解决的腐败,而今,更出现了断绝农民生存后路的腐败。
因此,农民为最后生存条件被剥夺而奋起抗争。以广州市近郊、远郊为例,一九九四年上半年,相继发生多起村民示威抗议政府无偿征地的严重事件。
从表面看,是乡村中共党支部或基层政府把其管辖区内的农用耕地,转让给国有企业,或卖给香港商人作商业开发用地,交易额少则数十万,多则数百万、数千万元人民币。村民的传统耕地被征用、转卖而得不到公平合理的补偿,有些官员在交易中贪污舞弊,更是激起村民愤怒抗争的重要原因。但从本质上看,却是农民为生存权而奋起的抗争。
抗争的首发地区,恰恰是对外开放、经济改革最早的广东珠江三角洲腹地,具有特别重要的民主特质。较之内地广大地区的农民,珠江三角洲农民具有特别浓厚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走出了人民公社的绝境,包产到户,争得种植自主权,扩大农贸市场,发展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个体经济得到初步恢复和增长,这段摆脱“计划经济”束缚的艰难路程,从一九七九年开始,足足走了二十年。终于,珠江三角洲农民觉醒了,要为自己最后的、也是最基本的权益——土地所有权而抗争。
打白条的劣根——统购统销
但是必须指出,与打白条弊端有直接关系的,应追溯到一九五三年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一九五三年十月起,中央决定对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产品,采取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即实施“统购统销”政策。根据有关部门统计,因经济建设而新增加的城镇人口约达一千七百万人,政府每年必须掌握七百亿斤粮食,才能有把握控制粮食市场,满足城镇人口能吃饱饭。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粮食统购统销采取强制手段,造成极其恶劣的后果。
二,一段“统购”试点工作的经历
笔者当年参加过广东地方的“统购”试点工作,现将这段经历,略述如下。
我们选定的试点工作村,叫新东锡,位于潮州城西十余里。
据介绍,新东锡村三百来户,一千二百多口人,多数姓卢。水田旱地约一千五百亩,实际水稻种植面积不到一千亩。由于地少人多,土地利用率极高。以水稻为主,还复种、间种小麦大麦、蕃薯杂粮、花生芝麻、各色各样的时鲜蔬菜。种植技术均做到深耕细作,绣花一般。产量很高,水稻年亩产近千斤。
接着,工作组召开全村群众大会。此外还分别召开党支部、团支部、农会、民兵、妇女等各种会议,反反复覆说明来意。但感到村民对收购粮食有抗拒情绪,村干部也有顶牛表现。后来找卢支书谈收购粮食的任务,卢支书只说了一句:我和干部群众再商量。掉头就走,不再照面。其它村干部和群众,见到工作组如同遇上痲疯病人,远远就躲开了,别说宣传党的“购粮”政策,连打声招呼都不可得,工作组束手无策。
这时,恰好省委一位大官前来试点检查工作,他就是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安平生。安部长带着秘书、警卫员五人,在区党委王书记陪同下,听取了我们工作组一天半的汇报,作了半天的指示。最后是王书记指示:按照安部长指示的精神办。
以阶级斗争精神落实政策
安部长的指示精神,照我们的理解,可以归纳为四个字:阶级斗争。安部长说土改结束才一年,地主富农和其它反动分子,美帝走狗、蒋匪帮特务分子,人还在,心不死,时刻都在反攻倒算。而我们的许多同志,脑子里面阶级斗争那根弦,早已松掉了,这是多么危险的和平痲痹思想!用这种思想来指导我们的农村工作,必然一叶障目,不见森林。把党的极其重要的农村工作,统统当作一种纯技术性的具体业务,那是十分有害的。凡是不从“阶级斗争”入手的地方,工作必定死气沉沉。我相信同志们必能鼓起勇气,发挥斗志,坚决落实“阶级路线”,打开新局面。
工作组很快就统一思想。组长立即召开党支部会议,把卢支书撂在一边,大讲阶级斗争,大批和平痲痹思想,甚至指着卢支书的鼻子骂了起来,说有的共产党员,忘恩负义,党解放了他,分土地给他,培养他入党,给他荣誉和地位,现在党要他卖几粒谷子,就像割他的肉,喝他的血,这样的党员如果不回到党的立场上来,迟早要滚到地主的地狱里去,永世不得超生!卢支书低着头,脸孔一下青一下白,最后流着泪说:我三代贫农,现在有了土地,家里有了几担谷子,高兴得睡不着。半夜起来,摸一摸几箩谷,就像大热天吃了一碗草粿,实在舍不得卖。不是忘记党的恩情,实是一时想不通。
“是否拥护党”的立场问题
斗争地富,三年前的老把戏,对于农村党支部书记来说,简直是“三个手指捡田螺”,十拿九稳。更何况,经过土改斗争,地主、富农的当家人大都已经死于非命,幸存下来的大都是一些妇女小孩。他们处于被专政的地位,日常生活受当地农会管制,不准“乱说乱动”,不要说反抗,连喘气的份儿都没有。
卢支书按照组长的指示,把全村的地、富及其家属都集合起来训话,然后逐户当众自报“不法”,连心里想过的什么“不满”、“不服”,都得坦白交代。再由农会会员逐户予以批判,认为是严重罪行,实时斗争,免不了拳打脚踢。最后一项是自报“卖余粮”,也是最艰难、最费时、最费口舌的新任务。
地富虽然按人口也分得一份土地,但贫雇�┫碛杏畔热ǎ侍锖玫卦绫环值簦O伦钍葑罨档摹杆蔡铩梗由侠土Σ蛔悖秩狈Ω骶楹妥式穑粘勺匀徊蝗缗┟瘢矶嗟馗患彝チ钡仄骄诹付即锊坏剑挠惺裁础赣嗔浮梗?p>逼斗“地富”卖余粮
此时,卖不卖余粮,自然就成为拥不拥护党的标志,立场问题、态度问题,甚至敌我问题,谁惹得起?至于有什么“实际困难”,自己想法子解决吧。于是“拉橡皮”,“挤牙膏”,一点一点将粮食挖出来。限时限刻,自己到粮站,送上门去“卖余粮”。
在逼斗地富卖余粮过程中,全村农民都受到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尤其是作为依靠对象的党、团员、民兵、贫雇农,都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只得按额按时,完成卖粮任务。
农民成为失去土地的农奴
毛泽东借重农民的力量打天下,为了取得农民的支持和拥护,把历年的战乱、农村的破败衰微、农民的贫穷,统统归罪于地主。一场历时三年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国传统的土地拥有者和经营者,即占农村总户数约百分之十一的所谓“地主阶级”、“富农阶级”、“小土地出租者”连同数百万人的生命,全被消灭了。维系中国三千年文明史的农业经济基础,被摧毁了;与农业经济不可分隔的城镇工商业,也遭受严重打击;甚至海外数千万华侨在国内的利益,也受到严重损害。而农民在这场“分田分地”运动中所分得的一份微薄土地(以广东为例,人多地少,一般只分到五分耕地),并没有因“翻身得解放”而点土成金,许多农民因为生产上所需求的资金、农具、种子、畜力、劳力、运输等重要环节得不到及时解决,反而生产热情下降,收获也不如前。更令农民心寒的是,政府发给的一张标志所有权的“土地证”,于五年后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变成一张废纸。本来薄有资产(土地、耕牛、农具)的农民,从此一律变成“无产者”,美其名曰“公社社员”,实则是失去土地的农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是一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宪法,实施公有制,废除私有制。私人财产不受法律保护,农民失去土地,和工商业者(资本家)在“公私合营”改造运动中失去财产一样,实际上是被政府“依法”剥夺了。
(争鸣2002年1月号) (余之夫 1/2/2002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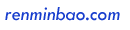















 打印机版
打印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