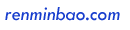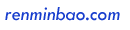|
【人民報消息】 ● 一.秋風蕭瑟: 「嘀嘀打打嘀嘀——」激越、尖脆的衝鋒號壓倒了曠野凌厲尖嘯的狂風,確實激勵、振奮起戰士們的勇氣,中朝邊境十月寒秋,一個小戰士,氣喘吁吁,端着日本三八式大蓋步槍上着刺刀,年紀不過十六、七歲,那付認真的神氣如臨戰場,真不像在演習。 連長的總結更精彩:一米八的高挑個,虎虎身姿,「今天打了個大勝仗」,戰士們肅立,不喊「稍息」,讓戰士們保持緊繃繃的挺胸雄姿,不像一般習慣,連長講話離連隊三米開外,而是緊貼戰士,雙拳輪番在戰士們頭上高低揮灑,強烈的鼓動象串串連珠炮彈在連隊上方低空炸響。 「我們是黨軍,……帶着強烈的階級仇恨練兵,美國鬼子就是地主老財的總代表、總後臺,…… 「今天的演習,刺刀見紅,殺出了威風,殺出了壓倒一切敵人的氣勢!……等於消滅了整連、整營的美國鬼子、南朝鮮李承晚匪軍!……」 「這才叫戰鬥動員、政治鼓動!不要小看華北部隊,好好觀摩!向友軍學習呀!」軍政治部何戰主任說, 「人家把總結戰術、技術放在其次,先講政治……」軍大老同學細高挑的鄧竹書祕書也讚賞不已。 「我們就需要這樣的幹部,軍事人員有政工人員的本事,這個幹部可以當教導員,是政治委員的材料」彭主任繼續評說。 在曾澤生手下當過國軍參謀和作戰科長的薩錫豪也說:「國民黨怎麼能不打敗仗,沒仇沒恨,提不起氣!」一邊波浪鼓般搖着頭。 這位紅臉連長疾風迅雷般的鼓動,似戰鼓聲催,使我也感受到:馬上投入戰鬥,發起衝鋒,全連會義無返顧,死而無懼。 夕陽西下,眼看就要被女臥佛一般的雞冠山遮盡,野風吹得高壓電線嘶鳴咆哮。 耳邊寒風響着尖哨,我不祥地聯想到荊柯刺秦王之前,在易水邊悲壯告別,荊柯好友高漸離擊築,合着粗壯音樂,荊柯慷慨悲歌: 「風瀟瀟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送行行列中「士皆瞠目,鬚髮盡豎」 看着連隊集體瞪圓的眼睛,我也感到頭髮上豎,根根直立…… ● 二.抖膽腐化: 邊境待命三個月,天天高粱米大鍋飯,換樣是玉米面窩頭,營房殘破透風,夜夜吹肚子,白天腹瀉,臨入朝爲將來負傷緊急輸血提前檢驗血型,小釘槍一砸耳垂,「嗡」的一聲,我失去知覺,休克了幾分鐘,耳聞「不要緊,不要緊,醒了」我坐在地上,原來摔了個「屁墩」,軍醫說:「缺乏營養,得多吃好東西。」 純粹廢話!師以上幹部吃小竈,營團幹部吃中竈,還得十年軍齡才夠條件。連排幹部和戰士同吃住,一律吃大竈大鍋飯。軍事共產主義供給制:沒有薪餉,戰士每月津貼三、四元爲買牙膏、肥皂、毛巾用;連排幹部七、九元,那時豬肉五角一斤,偶而外餐還夠用。 雞冠山小鎮,每路過飯館,鍋勺乒乓作響招徠顧客,我幾番猶豫沒敢進去,解放軍艱苦奮鬥沒有下飯館的,有些怯場。 部隊開拔到安東,市裏飯館很多,一次乍着膽子進一家朝鮮小館,空無一人,一位白衣白裙的老大娘從竈間迎了出來:「啞暴笑」,我不懂,嚇得轉身逃了出來。 「哎,小鐘,朝鮮館狗肉湯面,沒勁,走,走,跟我們打牙祭!」 鄧竹書拉住袖頭就走。酒樓字號記不清楚,樓上開了單間,薩錫豪坐在裏面,兩位過去的國軍軍官,實在吃不慣解放軍的革命飯,似乎常出來「打牙祭」,在國軍當過官,多少有些積蓄。 單間半截門簾,看到半截簾子下綠軍褲一閃而過,老薩掀了門簾追了過去:「李連長,這邊!這邊!」,看來這位連長也常甩開戰士溜出來打牙祭,和鄧、薩二位已很熟,今天老鄧請客:鍋蹋肘子,燒馬哈魚,肉絲炒酸菜,還有國軍官兵認爲最實惠的燉豬肉加粉條…… 來客就是那位會講話的連長,紅彤彤的蒙古臉型,顴骨較高顯得鼻子稍尖,誇大說有幾分象貓頭鷹,但年輕還算漂亮。 我提出存心已久的問題:鄧、薩二位的怪名字。 鄧說:「古書《竹書紀年》聽說沒有?沒有!小老弟書香門第,孤陋寡聞哪!漢以前沒紙,用刀或漆刻寫在竹片上,用繩穿起來就是竹書。」 「不談這個,不談這個,今天要多向大連長請教。」我也感到自己很不知趣,知道他們二位對被解放軍打敗,心裏一直不太服氣。 李連長見我在場,有些拘謹。 酒過三巡,鄧喝白蘭地,薩喝俄斯克,我喝茶,李連長專喝老白乾,臉更紅了,話匣子逐步打開: 「太太?我們叫愛人,一塊上小學,領到家裏,家長都喜歡,後來就結婚了。……」拉起家常,連長也有人情味,我對他有些喜歡起來。 談起國際局勢…… 「南朝鮮利用各種不同方式向北朝鮮不斷挑釁,最後發動了進攻。」李連長總是重複這一句。 「什麼各種不同方式?您詳細說說,具體點。」鄧問, 「利用各種不同方式」李還是那句話。 鄧、薩見他也不知道(人民日報也沒具體材料),漸漸轉向打仗的話題,…… 「大、小戰鬥百十來次,這一百來斤總沒報銷, ……」紅臉連長醉意陶然,開始無所顧忌。 ● 三.娓娓雄談: 「敗仗?怎麼沒打過?!聶榮臻部隊常打敗仗,打不過傅作義,王鳳剛的部隊很厲害。……」 「那就看你怎麼指揮了。……我在鋼鐵第一營當排長,早就看出哪個要開小差,我叫他替換機槍手,甩手一槍把他斃在那裏了,趴在重機槍上,正好象在瞄準,你們國軍一時半會兒訣不敢衝上來,撤!沒有一個傷亡。」 「碰到國軍大部隊怎麼辦?整連衝鋒,擋不住,死拼不行,我命令三個戰士跳出戰壕,分三路去拼刺刀,敵人圍成了堆,馬上命令機槍給我掃射,等到拼剩下來的人太少,剛好足以安全轉移,撤!」 「過封鎖線?層層碉堡?!正面是過不去,派兩個戰士從後門衝進去拼殺,裏面馬上亂了營,顧不上往外看……」 「那次是孤軍深入,跟你們四野尖兵衝進天津一樣,也是被殲滅了一個整營,打到最後就剩了我自己。藏在老鄉家:「大娘啊,實話對你說,三天沒吃飯了」到哪兒都得是這句話,河北人實在,大娘心軟,馬上烙白面餅炒雞蛋,把捨不得吃留着換錢的雞蛋都端出來了。換上大娘兒子的衣服,寫下欠條,摸回了部隊。」 「愛兵?怎麼叫愛兵?!革命有分工,戰鬥員就是打仗的,用在刀刃上就是愛兵,你們國軍總唱:射擊軍紀重要……隱蔽身體!怎麼發揚火力?兵趴在戰壕都槍管朝天」 鄧竹書又給斟上一杯,插嘴道: 「新兵才朝天放槍,老兵打日本鬼子,出生入死,打中國人狠不起來。解放軍怎麼訓練的?「政治練兵」?不懂!」 「日本鬼子兇,靠武士道精神,上當受騙。我們是革命英雄主義,戰士靠階級覺悟,四野解放東北一進關,四野政治部經驗介紹發到團營,過去搞仇恨傅作義教育不具體,戰士恨不起來,兩個月政治練兵,連炊事員伙伕都要求上前線,戰士們哭得眼都紅了,看歌劇《白毛女》,臺下開槍打死了臺上演地主黃世仁的演員,以後看戲,部隊不準帶槍。」 「你們沒見過訴苦會?臺上哭得淚人似地說不下去,臺下捶胸頓足,大家都成了親兄弟。」 「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嘛,有那麼多地主老財欺壓窮人的故事嗎?」鄧竹書問。 「有!有!戰士來自四鄉八鎮,俘虜兵五湖四海,全師選拔最典型的巡迴訴苦,假的也許有,沒法調查,有的造假讓同村的戰士揭了底,也只能壓住,那不能公開。」 「告訴戰士保田保家,美帝要打進來,地主就回來了,土地改革分到的土地浮財地主老財就要反攻倒算。」 「蘇聯土地可都收歸國有,戰士土地保得住嗎?」薩有所懷疑。 「中國的國情不同,共產黨起家靠農民,黨說話是算數的。」連長肯定地說。 「老兄犯過軍紀沒有?」薩錫豪問,打量着連長的臉。 「解放軍就兩套服裝,單衣凍死換棉衣,三九天不能讓戰士凍死,打進縣城,開倉庫,國軍棉衣堆成了山,我讓全排換了,犯了軍紀,排長撤了,鋼鐵第一營取消了,戰士含着眼淚向首長求情,沒半年官復原職。」 「佩服!吳起兵法講究,愛之如狡童,用之如泥沙!」鄧說 「是的!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當兵的留不住,就是用來打仗的。林彪的厲害就是敢拿戰士往裏填,帶兵的不能怕犧牲,四野的兵唱什麼?「上戰場,槍一響,老子下定決心,今天就死在戰場!」看人家兵練的!」 「兵字古代只當兵器講,士兵叫做卒,解放軍的兵就是武器。」鄧竹書忍不住掉書袋,搖頭晃腦。 李連長接着:「你看我們一打大仗,先保存幹部,成立教導隊,把各級副職上調保存起來,部隊打光了,有人帶新兵,這叫保存戰鬥作風,羊羣不散靠頭羊,鋼鐵第一營是井岡山老紅軍的底子,一茬茬換了多少代人,戰鬥作風保存到現在,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 老鄧一挑大拇指:「李連長真蓋了!精通林總的帶兵要領:政治第一,帶着仇恨練兵;犧牲少數,保存多數,捨車保帥。遼瀋戰役「關門打狗」,以大吃小,以數倍兵力包圍,在塔山、黑山阻擊敵人增援,就是死守,犧牲多少戰士在所不惜,打天津,一個營孤軍深入,也是必要的火力偵察,個人服從集體,局部服從整體。」 薩問:「怎麼講?」 鄧答:「怎麼講——社會主義陣營就是整體,中國是局部,舍多少兵也得去保斯大林大元帥,我們就是局部,就得衝進朝鮮社會主義橋頭堡裏去拼刺刀,你要想開小差,連長就給你一槍。」 薩吐舌頭,作鬼臉:「這麼說,咱們都是舍哥?」 「不,不,不,都是黨的親兒!」醉連長立即糾正。 當時是開玩笑,是不是舍哥也沒去想。入朝後真證實了鄧竹書的戰術邏輯,包圍、追擊敵人的部隊,士氣高昂,阻擊敵人突圍的部隊血肉橫飛,十不剩一。前三次戰役下來,第一批入朝的戰士都整整換了一茬。至於先期入朝冒充人民軍的第四野戰軍,朝鮮族四個師,更早早地成了犧牲品。 ● 四.風物長宜放眼量: 人的認識是遞進的,現實叫人睜開眼皮。 1964年,林彪當了國防部長,提出四個第一: 人與武器的關係?人的因素第一;
軍事與政治的關係?政治工作第一;
政治工作內部關係?宣傳工作第一;
宣傳工作內部關係?抓人的活思想第一。 1965年,電影《新聞簡報》上宣傳舍死忘生的戰鬥英雄麥賢得,賀龍元帥看望他說:「你是了不起的英雄,全軍都在向你學習。」但是麥賢得說不了話,也不能照例向首長握手。當時沒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