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六年过去了。虽然那枪声和火光,那倒在血泊中的孩子们的躯体还清晰地印在人们的脑海中,但到底有多少人死于那场屠杀,至今还是一个谜。因为中共政府封锁信息,拒不公布死者名单。但是,人民绝不会因为当局掩盖真相就忘记那些无辜的遇难者。
有血有泪,纸重千钧
不久前,朋友寄来一本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丁子霖在香港出版的《‘六四’受难者名册》。接到书的那天,我正忙于赶写一篇文章,因此只想粗略翻一翻她的书,以后再细读。但刚翻了几页,就放不下来,手中的书越来越沉重。这是一本“六四”遇难者的母亲用血和泪写成的书,这是一部凝聚着年轻的生命的碑文。丁子霖的年仅17岁的独子蒋捷连死于“六四”屠杀。面对当局拒不公布“六四”遇难者名单,用谎言掩盖“六四”真相的卑劣,丁子霖克服各种阻挠和困难,拖着病弱的身体,在偌大的北京城,一家一户地寻访“六四”死难者的情况。在过去的五年中,她终于寻访到了96名遇难者和49名致残者的个人情况。她将这些第一手资料编辑成书,用表格方式,列出死者的姓名、性别、年龄、生前单位、遇难经过和家庭情况,并有她写的寻访这些家属过程的文章。
对于“六四”惨案,外界只是通过媒体对宏观场面有所了解,而对遇难者的详情,则罕有所闻。这本书里的许多细节都是以前未公诸于世的。这本书所披露的死者年龄之小,当局镇压手段之残忍,和当局对遇难者家属的恐吓与折磨,都是外界难以想象的。
风华正茂,死于血泊
在“名册”中的96名遇难者中,22岁以下的就有28人。19岁以下的达10人,他们像丁子霖的儿子蒋捷连一样,仅是高中学生。书中有蒋捷连生前与他父母的合照,他比父母高出一大截。一个健康、英俊的小伙子,一个对未来充满了梦想与憧憬的微笑着的青年,人生还没开始,就被子弹射杀。遇难者中年龄最小的女性是19岁的张谨,她是北京职业高中毕业生。书中有一张她生前的照片:她依偎在一辆汽车前,戴着鲜红的围巾,甜甜地笑着,洋溢着天真和青春活力。难以想象,这样一个清纯的少女,竟被子弹射穿头部,死于血泊之中。
几天前,我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妻子的毕业典礼。看到那些年轻的学生们纵情欢呼,将博士和硕士帽向天空抛掷,并将威斯忌酒向人群喷溅的欢乐场面,我不禁想到那些倒在天安门广场的孩子,如果他们不被子弹夺去生命,现在也该是大学或研究生毕业,也会这样兴奋地走出校园,去创造斑斓的人生。但他们的血肉却永远地与天安门的土地联结在一起,死得那么早,死得那样惨。
在“名册”中,有很多是应届毕业生。22岁的吴国锋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应届毕业生。他是父母的独子,来自四川一个贫穷偏远的县城,是该县唯一的一个大学生。考上大学时,全县几十人给他送行。全县才出这么一个大学生,竟死于枪口。清华大学建筑系应届硕士研究生何洁,被称为“神童”,他15岁上高一时就被清华大学录取为大学本科生。遇难时他已学完硕士课程,还不满22岁。人们常说“孩子是祖国的花朵”,可这些才20岁上下的含苞未放的花朵,竟被邓小平苍老的手残忍地一支支掐断了。
疯狂坦克,疯狂政府
在“六四”屠杀中当局是否使用了“炸子”,即国际上禁止使用的射入人体后爆炸的“达姆弹”,一直众说纷云。丁子霖的“名册”这次提供了准确的证据:有8人死于“达姆弹”。被这种特殊子弹打死的大学生钟庆和安民都是半边脸被炸飞了。北京国际广播电台俄语部副主任张汝宁和市民杨明湖都是腹部中了“达姆弹”而死亡。杨明湖的膀胱和骨盆被炸得粉碎。善良的中国人当初还以为当局用的是“橡皮子弹”,但“解放军”却用了比一般真子弹更可怕的“炸子”。
同样残忍的是戒严部队的坦克竟横冲直撞,将人活活碾死。看过“六四”时电视新闻报道的人都会记得,当晚在长安街上有一辆疯狂飞弛的坦克。据丁子霖的寻访调查,仅是这辆坦克,就碾死四人,压残八人。这死伤的12人都是大学生。22岁的田道民是北京科技大学管理系学生,当夜清晨,他刚刚写完毕业论文,走到六部口,就被坦克碾死。21岁的王培文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八八级学生,他站在从天安门广场撤出的学生队伍前排,走到六部口,被迎头冲来的坦克当场碾死。王培文的同班同学,年仅19岁的董晓军走在队伍后面,被由后至前的坦克撞倒,尸体被轧碎。在战场上,战士被坦克碾死的也不多见。让人难以想象,一个手无寸铁的19岁的孩子,竟被坦克有意地从后面追上来活活地压倒碾死。子弹有时可以不长眼睛,但开坦克的人通过仪器是清楚地看到坦克外的一切的。这名军人要有多么邪恶的心才能干出这样毫无人性的事。而中共的领导人们要有怎样的兽性心肠,才能下出这样的杀人命令。
同样悲惨的是,有的学生被坦克碾成了终生残废。23岁的体育学院学生方政,见到坦克向人行道上的女学生压来,为抢救同学,他的双腿被坦克碾得血肉模糊。在医院,他的两腿从大腿根处被截去。他酷爱体育,坐在轮椅上,仍苦练铁饼投掷,五年后终获全国第一的成绩。当他参加国际残废人比赛时,当局得知他是“六四”之夜致残,取消了他的比赛资格。 血腥之夜,故意杀人
“名册”中,附有丁子霖写的多篇记载死者遇难经过的文章。那些沉重的铅字,刻记着那个夜晚的种种血腥:
19岁的北京市五十七中学高三学生叶伟航,右肩和右胸中弹后未死,倒地后右脑又被士兵补了一枪。20岁的北师大经济系学生熊志明,和班上一女同学躲进一个胡同,戒严部队士兵追进胡同,将他们俩人都射杀。
24岁的清华大学化工系应届毕业生段昌隆,见到戒严部队与群众对恃,为防止流血,上前劝说军人不要开枪,刚走到戒严部队前,一军官拔出手枪射中他的左胸致死。医生从枪口也研判出,他为小口径手枪近距离射杀。段昌隆的父亲段宏炳是北京西城区政协委员,他44岁才得这一独子。段昌隆的死使段家断了后。段昌隆也是北洋军阀段琪瑞的侄孙,他的遗骨安葬在京郊万国公墓,与他的叔祖段琪瑞的墓在一起。当年段琪瑞镇压学生,在北京执政府前打死了40多人,酿成“三‧一八”惨案。事隔63年,他的侄孙风华正茂,也是学生,在同一地点被中共政府枪杀。段琪瑞九泉有知,不知会做何感想。 六四之后,继续屠杀
“六四”过后,北京政权操纵宣传机器,称屠杀为“平暴”,说是“迫不得以”。最近在海外也有人批评学生当时坚持在天安门广场太激进,因为他们阻碍了政府的“清场”才刺激当局使用了武力。丁子霖的“名册”证实这些说辞都违背事实。因为“六四”过后,学生已完全撤出了天安门广场,戒严部队也没踫到“迫不得己”的情况,但仍有学生和市民被枪杀:
北京时间六月五日凌晨,21岁的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编采专业应届毕业生钱辉,在他学院门口,被坦克射出的大型子弹射中腹部,另一枪打断大腿动脉。当时未死,还向同伴说了一句;“当心!军车还没有过去!”同伴把他抢救到校门内,血流一百米,死去。
六月五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萧杰,在行走至北京南池子南口,过马路时越过了警戒线,戒严部队喝令他站住,随后一梭子弹从后背穿胸,他当即死亡。年仅19岁的萧杰是他父母的独子。
六月六日,即“六四”屠杀过后第三天,在北京复兴门外大街,戒严部队又杀戮平民,致使三人死亡,三人致残。该日下午三点左右,一个13岁的男孩放学回家途经木犀地地铁口时,遇到几辆坦克。突然一辆坦克用机枪向四周扫射,小男孩胳膊和腹部中弹。行人欲将小男孩抬送医院,坦克上士兵举枪威胁,不准向前救护。孩子倒在血泊中抽搐呻吟约半小时,一位老者实在忍不住,向戒严部队高喊“拥护平暴”,并哀求说,“这孩子还小,不是暴徒,让我把他送到医院吧。”才算获准。在复兴医院手术七个小时,孩子命保住了,但成了残废。
六月六日晚上,五男两女七个青年在走到南礼士路时,被戒严部队喝住,随后一排子弹,将五名男青年射倒在地。送医院抢救后,五名青年有三人不治身亡,两名致残。
六月七日晚上,建设部中国建筑技术研究中心《村镇建设》杂志编辑安基与另五名青年(三男两女)在经过北京儿童医院时,被戒严部队喝住,在一阵射击中,安基和另一青年同时中弹身亡。两名女青年因跪地求饶才幸免一死。
即使按照北京当局的说法,“六四”屠杀是“迫不得己”,是为了天安门清场的需要,但六月四日以后对平民的这些故意杀戮,又怎样解释呢?
暴政不亡,天理何在
中共当局在屠杀了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市民后,还继续对死难者的家属进行恐吓和折磨。“名册”列出的96名遇难者中,只有两名死者的家属,即蒋捷连的父母蒋培坤、丁子霖和段昌隆的父母段宏炳、周淑庄愿意公开死者家属姓名、直接与外界联系。为什么其它94名遇难者家属要保持沉默呢?是什么力量,使他们自己的家人死了,他们还不敢公开身份,寻求一点资助?而且他们的生活都很艰难,多是上有老、下有小,孤儿寡母,支撑度日。27岁的北京大学化学系讲师萧波遇难时,留下一对才出生70天的孪生子27岁的北京市煤气公司车队工人王建平遇难时,他的一对双胞胎女儿才八个月。北京弹簧厂汽车队队长周永齐遇难时,他妻子刚分娩15天。他们多么需要外界的支持帮助啊!但当局以各种手段威胁恐吓他们,不准他们公开遇难者家属身份,说出实情。萧波的妻子带着他们的孪生子几年来一直隐名埋姓,深居简出。原因是“北大”校方与她“有约”在先:不准透漏萧波的遇难经过;不准披露她是遇难者家属;不准接触外国记者。否则不得住在学校的房子。不要说公布死者遇难的经过,即使遗体火化,也要有公安局开具的不是暴徒的“身份证明”。丁子霖在她的书中写道:当局“对有些死者家属实行监控,通过街道或居委会监视死者家属与外人的接触和来往信件。有的家属不时受到盘问。连清明节和‘�摹苣昙沂羯梗本忠驳髋纱罅烤种刃颉沟亓肿趴植赖钠铡!?
北京家用电器研究所工人刘燕生遇难前单位曾给每位职工投有生命保险五千元。当他遗孀带着11岁的孩子找到那家保险公司时,得到的答复是:按政府规定,此次事件中死亡者不予赔偿。
另一位遇难者的妻子,带着五岁的孩子去找丈夫生前单位求助,单位答应给八百元人民币抚恤金,但要她在她丈夫“正常死亡”的书面结论上签字。她拒绝了。她说:“这不是事实,我不能对不起死者。”
自己的家人被无辜杀害,家属还要被羞辱欺负到这等地步,这是一个怎样不讲一点人性的政权!这样的政权不灭亡,天理何在?!
谁是凶手,一目了然
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曾多次表示,在适当的时候要公布“六四”死者名单和死亡人数。但至今已整整六年过去了,中共没有公布任何名单。是因为情况复杂统计困难吗?不是。因为以中国大陆实行的那种严密的户口和档案制度,以六年的漫长时间找出遇难者是谁,整理出一份死者名单并非难事。而且,中共政权向来善于将人分类,列出“名单”。不久前,外界还拿到北京政权编篡的一份将海外民运人士分成三类,不准他们入境的“黑名单”。北京政府对海外的中国人都能分门别类,查个底朝天,怎么对国内握在自己手掌心的人整理不出一份“名单”呢?中共不仅拒不公布“六四”遇难者名单,连他们奖励的所谓“平暴”有功的“共和国卫士”的名单也不敢公布。既然是“平息反革命暴乱”,为什么不敢公布那些“卫士们”的赫赫战功和鼎鼎大名呢?这一切只能说明北京政权实在是理亏心虚。因为只要死者名单一公布,人人可以看出,谁是真正的暴徒和杀人凶手,谁是受害者。
读读名单,净化灵魂
丁子霖完成这样大规模的寻访调查非常不易。而且她身患多种疾病,身体很虚弱。据最近在大陆见到丁子霖的一位华侨回来描述,丁子霖与他谈话半小时,就喘得必须躺倒休息几分钟。偌大个中国,只有丁子霖去默默地做这件遇难者名单寻访工作,令人深思。
当然,丁子霖寻访调查到的九十六名遇难者远不是“六四”遇难者的全部。但这份名单清晰地反映了“六四”事件的本质,它是一场对平民的血腥屠杀,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这份“名单”是铁的事实,是血的控诉,是生命的证据!它展示了共产主义邪恶的程度,也展示了人类维护尊严、抗争邪恶的不屈精神和付出的代价。一年前,反映犹太人在二战时被人营救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轰动全球,获得“奥斯卡”。“辛德勒的名单”记载的是免遭纳粹迫害的幸存者。而“丁子霖的名单”记载的是为了中国人的未来而献身的牺牲者。这份“名单”更沉重,更珍贵。
但愿更多的中国人手里有一本“丁子霖的名单”,不时看看,翻翻,让那些为中国的未来而遇难的孩子们的微笑,净化一下我们的灵魂,唤醒一下我们的良知,提醒一下我们的责任。
(载1995年6月4日纽约《世界日报》周刊)
“ 六四遇难者名单”摘选
吕鹏,男,9岁,北京顺城根小学三年级学生。6月3日夜12时,在复兴门立交桥附近胸部中弹,当场身亡。
周欣明,男,16岁。6月4日遇难,葬于金山陵园。
蒋捷连,男,17岁,中国人民大学附中高二学生。6月3日夜11时于木 地附近后背中弹,经送市儿童医院抢救无效身亡。父母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副教授。蒋捷连为其父母独子。
刘洪涛,男,18岁,北京理工大学工程光学系88级学生。6月4日凌晨在民族文化宫附近被射杀。
王楠,男,19岁,北京市月坛中学高二学生。6月4日凌晨在南长街南口头部中弹倒地,戒严部队禁止救护队抢救,两、三小时后身亡。其尸体当即与其它尸体一起埋于天安门西侧北京市28中学门前大土坑内。6月7日,尸体发出异味,经校方交涉,将尸体挖出,因王穿著学校军训的军服,被疑为戒严部队士兵,所以该具尸体被送救国寺医院,其它尸体遭火化。其家人6月14日才找到王楠遗体。
萧杰,男,19岁,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88级学生。6月5日下午在南池子南口,过马路时逾红色警戒线,戒严部队喝令其站住未听从,一梭子弹从后背穿胸,当即死亡。父母为一般干部,萧杰为其父母独子。
孙辉,男,19岁,北京大学化学系88级学生。6月4日晨在西单被射杀,横尸街头。
张谨,女,19岁,北京职业高中外贸专业毕业生。6月3日夜11时,与男友一起躲进民族宫附近的胡同里,遭戒严部队扫射,头部中弹,凌晨死于邮电医院。
龚纪芳,女,19岁,北京商学院企管专业88级学生。6月4日凌晨,自天安门撤到六部口,左臂中“炸子”,并因毒瓦斯造成昏迷,送市急救中心抢救无效身亡。死亡证书载明:死因主要是由毒瓦斯造成肺部糜烂。
董晓军,男,19岁,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工系88级学生。6月4日凌晨,董站在从天安门广场撤出的学生队伍尾部,被由后至前的坦克压死,尸体被碾碎。
冰,女,19岁,北京广播学院88级学生。因参加八九民运受审查,过不了关,于89年9月中旬从学校塔楼13层上跳楼自杀。死前10分钟还给宿舍打过几壶开水,并留有遗书。
张向红,女,20岁,中国人民大学国政系87级学生。6月3日夜11时躲在前门西侧树丛,被子弹击中左胸,送市急救中心,凌晨去世。
王争胜,男,20岁,华北物质局职工。6月7日晚11时,经儿童医院附近,被戒严部队喝住,随后被射杀身亡。其兄王争强也在场被射伤。
贲云海,男,22岁,北京市广安门内街道办事处职工。6月3日夜,离家未归,次日在复兴医院找到尸体,腹部中了“炸子”。
田道民,男,22岁,北京科技大学管理系85级学生。6月4日清晨,田做完毕业论文后去六部口,被坦克碾死。家在农村,有兄弟姐妹8人,仅他一人上大学,家境贫寒,他的同班同学相约每人每年给田的父母寄10元钱做生活补贴。
宋晓明,男,32岁,航天部二院二八三厂工人。6月3日夜在五棵松附近被子弹打中大腿,送301医院,持枪的军人命令医生不准抢救,不准输血。因流血过多于凌晨死亡。
袁敏玉,男,35岁,北京地质仪器电焊工。6月3日夜,在三里河与木 地之间,胸部中弹,次日下午于儿童医院去世。遗孀袁静芬带10岁孩子,老父袁长禄为退休炊事员,现病瘫在床。老母病故。弟患精神病,住康复医院。幼妹植物人在家。长妹顶替父当炊事员。特殊困难户,可接受救助。
穆桂兰,女,48岁,北京国棉三厂工人。6月4日清晨6点半,穆出门买早点,路过朝阳门立交桥,遇坦克、军车自通县方向开来,一路射击,穆头部中弹,立即身亡。路人曾照相为证,并寄给其家人。
马承芬,女,55岁,49年参军,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6月3日晚,与楼内邻居在院内(水力科学院门前)纳凉,遇从东向西去的军车射击,腹部中弹,送医院抢救无效,凌晨身亡。马承芬的丈夫为离休军人,他多次就此事向军队系统写信反映,一直无回答。
注:此名单摘选自丁子霖的《‘六四’受难者名册》一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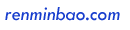






















 打印机版
打印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