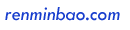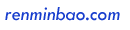|
【人民报消息】作为一位社会化的学者,我经常有幸接触到各阶层人士,并听到来自各阶层的不同声音。正是这些诉求各异的声音,使我深深触摸到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我真切地感到,这些声音引起的社会关注有大有小,原因倒不在于声音本身的高低,而在于发出声音的人背后的实力支撑。 人类社会从来就是靠实力排座次。在国际事务中,各国完全凭借以武力、经济实力为主要内容的国家竞争力发言;在一国的内务中,各阶层则凭借其拥有的实力发言,这实力,既有他们在社会阶梯上拥有的政治权力,也有货币赋予的权力。与这两项权力完全无缘的阶层,其利益诉求则有可能被湮没在历史的滚滚烟尘之中。 几种利益的诉说 今年4月底,湖南卫视“有话好说”节目请我做嘉宾。这次节目谈的是广州南方大厦企业集团公司25位下岗工人与该公司之间的一起住房纠纷。事情其实并不复杂,大致情况如下:1994年“南方集团”搞房改,这25位“南方集团”的职工还未下岗,就与其公司签订了购房合同,并按企业规定交了款,购买了该住房的使用权。但事过几年,政府下达了一个文件,规定房改不规范的企业必须重新进行房改。文件下达之时,这25位职工都已下岗,于是企业就根据政府文件,声称以前的购房合同不合法,必须重新来过。鉴于这25位职工都已下岗,请他们从现有住房里搬出去。这一下25位职工都傻了眼,因为他们处于失业状态,根本无处可去。如果放弃现有住房,就只有流落街头。这25位工人当中,工龄最长者已在这个企业里工作了近30年,最短的也在这企业工作达十余年。他们认为企业不应该将他们赶出来,于是据理力争,希望保住这点可怜的权益。结果官司打到当地法院,当地法院按照政府文件判决,认为原合同属于企业行为,不具合法性,应当作废。这些工人求告无门——广州传媒本是全中国最发达的,但不知道这事为什么会被当地传媒给漏掉了——于是有人将他们的案子作为新闻线索提供给湖南卫视,与广州没有利害关系的湖南卫视就邀请他们派出几位代表到长沙,在“有话好说”节目里讨论这一纠纷。 这个节目共邀请了数位嘉宾,一位是长沙某国企的赵厂长,另一位是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陆先生,还有我与一位“南方集团”下岗工人的代表,台下则是其他几位没有上台的下岗工人代表、从湖南几所大学里请来的几十位大学生、当地一些机关干部及其他身份的市民。节目形式是先由节目主持人叙述了这一故事,再由各位嘉宾谈自己对“南方集团”此举的看法。 最先发言的是长沙某国企的赵厂长。他表示理解“南方集团”这一做法,因为“南方集团”还有许多在职职工的利益需要考虑,国企改革显然需要牺牲一些人的利益。做厂长经理的也是人,他们也有许多难处,在追求效益的压力下,很难兼顾到所有职工的利益,只能是牺牲少部分人的利益以保证大部分人的利益。“人说改革难,就难在这里。再有能力的厂长也无法做到保证每个人的利益,只能狠狠心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以保证大多数人的利益。” 赵厂长的说话遭到了陆先生非常强烈的反对。陆先生表示,这对这部分被牺牲的工人来说绝对不公平,这些工人辛辛苦苦做了几十年,况且买房也付了钱,凭什么将人家赶出去?“南方集团”是家大公司,这房子看来也不是什么好房子,值不了多少钱,就算将房子收回去,难道就能救活这个企业?原来好几亿的企业资产,企业都搞不好,收回这20多套房子,百来万元钱就能救活这企业? 主持人问陆先生,如果请你来管理这个厂,你打算怎样管理?陆先生显然没想到有此一问,怔了一下以后很快回答道:我会与工人一起同甘共苦,吃咸菜稀饭也要将这个工厂搞好。 听众席的听众不满意了,一阵小小的骚动。主持人转而问下面的听众:“假设各位是那个工厂的工人,你们是不是只需要一个与你们一起喝稀饭吃咸菜的厂长?”听众还比较理性,知道这精神在如今已属稀缺物品,没过分打击陆先生的热情。一位男青年站起来说:“我们既要厂长能与我们同甘共苦,更要厂长能为工厂带来效益。如果一位厂长经理仅仅只能与我们一起喝稀饭吃咸菜,显然是不够的。” 主持人请我谈看法。我说:“今天这场面真应了一句‘文革’时期的老话,叫做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这位下岗工人代表正好是边缘化阶层的代表,而这位赵厂长则是经济精英的代表,陆先生则代表了知识分子中同情弱势阶层的那部分人。” 主持人继续问我,现在法院判决工人们败诉,要他们搬出去。而这些工人都无处可去。在这个案例中,到底是维护法律的尊严重要,还是同情弱者重要?我回答说:我们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法律制度还很不完善,需要从实践中不断摸索。法有恶法,也有良法,如果与社会道德及基本价值观背离太远,那就是恶法。更何况有关职工购买住房的政策规定还不具有法律效力,法院判决时也未充分考虑这批工人与这家企业的历史关系以及已形成事实的房屋买卖关系,所以目前的问题还不是维护所谓法律神圣性的问题,而是要回到如何保障劳动者的基本合法权益这一问题上来谈。也就是说,企业必须保证职工的合法权益,包括住房权益,简言之,就是不能赖掉历史债务。 接下来是台下的听众们发言。先是一位在长沙市政府房改部门的一位先生发言。这位先生提了个建议,他说长沙现在正在建设解困房,大概十万元左右一套,这种房子广州早已在建造。既然有了政府的解困房,根本就不必要再花精力去与“南方集团”打什么官司,还是想办法去申请一套解困房比较省事。坐在台上的下岗职工代表苦笑着说:“广州是有政府的解困房,可我们这25位都是已失业好几年的人,手中哪有余钱去买解困房?”我坐在台上,听着这话,不由得想起晋惠帝问他的大臣,那些饿死的老百姓“何不食肉糜”这个典故来。 接下来是几位在校就读的大学生发言。一位长得比较结实且活泼的女孩子有条不紊地谈了她的看法:“现在是市场经济,提倡竞争,这就注定了有胜有败。如果所有的下岗工人都不将占住企业的房子退还给企业,企业就会被拖垮。我认为这些下岗工人的处境确实值得同情,但不能因为同情工人而拖垮企业,那样会害了更多的工人。我认为这25位工人的住房合同在政府规定颁布之后已失去法律效力,应该搬出去,不应该将自己的负担强加到企业头上。刚才陆先生讲自己愿意与工人一起吃咸菜喝稀饭共度艰难,我也不赞成。这种精神虽然可贵,但是企业不是依靠吃苦精神就可以生存的。如果我是工人,要我参加选举厂长,我就不会投陆先生的票,因为我认为他没有做厂长的能力。”她的话马上博得了听众席上好些年轻大学生的掌声,不过我分不清这些掌声是为企业行为鼓掌还是为她针对陆先生的表态而鼓掌。 另外一位大学生站起来发表他的看法。这位大学生可能读过不少关于竞争法则的书,谈起来头头是道,包括社会达尔文主义那种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道理都成为他旁征博引的佐证材料。阐述了这些竞争法则以后,他发表看法:“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慈不将兵,义不掌财’。如果每个企业家都像陆先生那样,那就去开慈善院好了。”这话听得台上的赵厂长频频点头,台下也有响起好几次掌声。然后这位大学生直接要求我发表看法:在这种高度竞争的社会中,讲公平是否太理想化了一些? 我对这位同学说:从世界历史经验看,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确实是非常残酷。在那时候,竞争中的优胜者获得的奖券是货币,他们用来喂猫养狗的食物也比贫困者用来哺育后代的食物要好得多。但正因为少数富裕者的幸福生活与广大劳苦大众的贫困生活形成的反差太大,所以当时的阶级斗争非常激烈,这才有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问世,才有后来席卷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共产主义运动。马克思对当时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的猛烈批判,有如一面镜子,让世界在这面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丑恶,才有了资本主义世界后来的不断改进与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而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其实就是人类追求社会公平的一种表现,体现了社会对弱者的一种关怀,它消解了社会冲突,缓和了社会紧张状态,有利于社会进步。我们现在的问题在于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却一下将弱者推到了无法生存的境地。具体到今天正在谈的这个问题上来看,这25位工人在青壮年时期都在这企业工作,而企业当时的工资其实只不过是基本生活费,住房、养老、医疗、子女的教育等一切费用都是作为企业的一种社会福利分配给企业职工的。这是企业对职工的一种历史负债,更兼这房子还是他们未下岗时按企业要求付清房款购买下来的非产权房,享有居住权,现在企业不但不还历史欠债,连这个合同都不承认,这等于双倍的剥夺。这些工人有权继续住在里面,大家要想清楚此案的特殊性,不要简单地将其等同于一般的在市场竞争中落败的失败者。 讲完了这段话以后,我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请发言者补充一下他们的出身,父母亲的职业与家庭经济状况。已发过言的几位自报家门,基本上都出身于干部或知识分子家庭,家庭经济状况属于中等状态以上。 台下早有几位大学生满脸不忿之色,坐在第一排的一位举了好几次手,可惜主持人没看到。坐在中间的一位大学生终于得到了发言机会,他还未讲,就已泪流满面。但他说话清晰,非常诚恳。话虽然不多,但我至今还记得非常清楚。他说道:“我的父母都在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韶钢’工作,从我爷爷那一代开始参加建厂,直到我的成长,我们一家的命运都与那个厂子息息相关。可以说,那个厂是我们的家,不少类似于我这种情况的家庭也将这个厂看作自己的家。我们这个厂曾经是当地的经济支柱与税收大户。但现在那个厂已经停产好几年了,不是别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产品卖不出去。我的父母,包括其他许多人都很勤劳——我爷爷是个老劳动模范,我妈妈也年年评上先进。但现在他们都待岗在家,没有新的工作机会。大家都感到自己就像被家庭抛弃的孩子,无依无靠。我前年考上了大学,爷爷送我上车时对我说,孩子,再也别回这个地方,到别的地方去找条生路吧,这里眼看就要荒了。大家认为竞争中的失败者就该被工厂赶出去,我听了这些话心如刀割。国有企业工人的失败怎么能归结为他们个人的无能呢?我知道现在不讲同情心,但人没有同情心又怎么算得上是人呢?这些广州工人在讲他们的困难处境时,我就想起了我的爸爸妈妈,想起了我们厂里的下岗工人。他们是不是有一天也会被人赶出家门呢?”讲到此处,这位学生已经泣不成声,全场静默。 坐在前排的那位男青年再也忍不住,站起身来高声发言:“这个社会不公平!我们父母这一代是吃定了亏,但对我们来说,这种不公平还刚刚开头。我马上就要毕业了,家里有背景的同学早就找好了工作,他们的学习成绩不比我好,只是他们的爸爸妈妈比我的爸爸妈妈有本事。所以大家都说,毕业找工作,不是本人条件的竞争,而是整个家世背景的竞争。” 台下又有好几位站起来,争先恐后地要求发言,有的大声说,社会难道真要抛弃工人阶级了吗?主持人看到情形不对,连忙告诉大家时间已到,还要请职工代表发几分钟的言,算作结束语。 这个节目过了一周以后播出,但是我没看。因为我知道许多场景并不一定能播放出来。而那天谈到的两个企业恰好我都去过。如南方大厦企业集团,十二年前我曾作为深圳企业文化考察团成员随团去参观过。那时它是广州十大明星企业集团之一,是广州国有企业的骄傲,也是对外展示的样板。但过了几年以后,我就听说它不行了。但我没想到的是,十余年间这个规模很大的企业竟破败如斯,甚至将榨取工厂资产残余价值的主意打到已经卖过一遍的职工住房上来,从中可以窥见其破败之严重程度。 “韶钢”我也于1996年下半年去过。那时我在暨南大学经济系教书,曾去韶关考察。韶关钢铁厂当时已有70%左右的车间停产。党委书记是个精瘦的中年人,他对我们说,不要对我们谈国有企业的困难,什么企业办社会、冗员过多、效率低下,我们都知道,而且也知道原因。问题是怎么解决这些困难,但这已经超出单个企业的能力范围。接着他谈到韶关钢铁厂为解决几万职工的生活出路,曾想过种种方法,但都因“韶钢”的特殊地理环境而不能实施。一是距离韶关市区太远,几十公里路。职工无法到市里做小买卖,而重庆钢铁厂因距离重庆市近,已通过帮助职工做小买卖成功地解决了一部分人的生活出路;而“韶钢”只是一个钢铁城,大家都穷,在城内摆卖,你卖给我,我卖给你显然赚不到什么钱。二是韶关本身经济不发达,国有企业一片萧条,当地失业下岗员工本来就已经够多,小买卖早已饱和,街上到处都是用摩托载客的失业员工。这种情况下,“韶钢”职工很难到韶关市谋生。 国有企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的兴衰,带给几代人的幸福与痛苦真还不是纸面上那些文章能够讲清楚的。从理论上讲,我知道每一次社会转型期都会有一批搭不上便车而被甩落的不幸者。但我却始终无法忘记那天那位大学生那张淌满屈辱伤心之泪的脸。再过两年,他就要毕业了,但愿在目前这种知识型劳力普遍过剩的状态下,他能够幸运地找到一份适合他自己的工作。因为这对他那个家庭来说,他有一份工作实在是太重要了。 我默默地祝福着这位青年人。 “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 两个半月以后,我又到一个比较特殊的MBA班讲学。说这个班特殊,是因为这个班的学员们身份比较特殊,大都属于“成功人士”之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成功人士”主要是经济精英,中国知识界大都将中国未来的希望寄托于他们身上。 据介绍,这个班是欧共体与上海一著名大学联合办的。学员来源有三类:一是政府部门的干部,学费收35000元;二是国营大中型企业负责人,学费60000元;第三类是民营企业家,学费18万元。学员们属于前年报纸上猛炒的那类开着“奔驰”之类进学校的“老板”,其住宿条件当然与一般学员们大不相同。我问他们,为什么花这么大的代价进这个学员班?他们的答复倒也直截了当:一是觉得这个班的名声好,讲起来“牛皮”;二是可以在这里结交一批精英,这个班的学员,本身就构成了一个非常有用的社会关系网络。 我想起西方一些石油大亨、王公贵族们将自己年幼的子女们送进一些著名的私立学校念书,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让子女们将来长大成人后有一个现成的同学关系网利用。 这类成功人士在深圳我曾见过好些,大都属于这种类型:受过一定教育,平时也读些书,从伟人传记、世界名著到网络,基本也都在他们视野之内。经济管理类书籍是阅读重点。个别特别爱读书的人还知晓当前中国学术界的当红学者是哪些人。他们的家庭出身不一,既有出身于一般城市平民(包括小知识分子)家庭,也有出身于中、小干部家庭,还有个别出身于农村的。不过,他们现在的政治态度似乎与家庭出身关系不大,主要由他们目前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决定。 我讲课的内容是分析中国当前经济形势及近中期走势。虽然部分“新左派”因为我不提倡“革命”,早已义愤填膺地将我踢出了“工人阶级与下层人民代言人”的队伍——其实我本来就不敢以“人民利益的代言人”自居,因为没有任何工农群体通过一定的选举形式将这一桂冠赠送给我——但在这类成功人士眼里,我确实是与他们的主张很不一致。两天的接触过程中,负责接待的一位MBA学员,某民营大公司的总经理L先生,就不断与我谈到他们与我之间的分歧。因为不是第一次接触这类成功人,我倒是更愿意听他们多谈谈看法。那位负责接待的L先生说话之前总是以“我这个想法你肯定不赞成”、“我这个说法你肯定要反对”作为导语,听到后来我只得声明:“我的想法你们可能从文章里面也知道了,请别先假设我会反对你的想法。我想多听听你们谈自己的想法”。 来听课的人基本上都属于成功人士。由于是分析中国近期经济走势,我逐一就八十年代以来发生的许多问题进行分析以后,不少前来听课的人士纷纷就演讲内容问了一些问题。那些提问我大多已记不清了,只有一位先生反复陈述的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看法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得他问的是我认为中国需不需要政治体制改革。我的回答是:“中国的改革现在进入了一个瓶颈,所有的问题虽然发生在经济领域,但其根源却深植于非经济领域。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加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将进入死胡同。历史上大规模的社会变迁都是都包含三方面内容,建立在宪政基础上的政治体制改革,以财产所有权为核心的财产所有权变迁,意识形态的变迁。我们二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仅仅只是社会变迁的一个方面。”这位先生听后很明确地表达了他的看法,认为中国目前无论是经济形势还是社会安定团结方面都很不错,虽然有些问题,但总体来看,经济体制改革很有成效。最后他总结说:“我认为,中国至少十五年内不要搞政治体制改革。因为苏联东欧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前车之鉴,如果现在搞政治体制改革,一旦失控,像苏联东欧那样发生社会动乱怎么办?”我当时是半开玩笑地说:“你为什么不要求五十年内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啊?那时候咱们都不在了,不是什么风险都不用担了吗?”听众们哈哈大笑。 L先生约好第二天晚上请我吃饭,还有几位在大企业任职的经理想一起聊聊。我告诉他,还有两位朋友Z先生与X先生将来看我,不知能否安排出时间吃饭。L先生表示对这两位先生亦慕名已久,能否请他们一起谈谈?我于是大包大揽地代两位朋友答应下来。第二天下午Z、X二位来宾馆看我,聊了一阵天以后,我代L先生发出邀请,并说晚上我们要尽量少说话,听听他们谈什么,可能更能帮助我们了解中上阶层的政治态度与社会参与意识。他们也觉得此主意甚好,于是答应下来。当天晚上来了四位“老板”,两位是民营企业老板,两位是国有企业的经理,即所谓“假老板”。这些人素质都不低,见识谈吐都属于九十年代崛起的、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代知识型企业家。 一位国营企业老板侃侃而谈。他说,国有企业现在的情况大家都知道,说是保卫国有资产不流失,其实没用,目前正在加剧流失,剩下的也没多少好资产了。如果再这样下去,国有资产就会什么也不剩。还不如现在瓜分掉,集中到一些能者手里,说不定还可以干点事情。我对他说,问题不在于分不分家,而在于按什么原则瓜分国有资产?并确定哪些人有资格参加瓜分?这位先生的回答很坦率:知道的人就参加分配,不知道的人就不参加分配。我请他解释,所谓“知道的人”是不是指有权力者?如果是,那么“不知道”的人怎么办?这位先生坦然答道:“‘知道的人’就是有权力参与瓜分的人。‘不知道的人’就是指没有权力参与瓜分的人。不过有些‘不知道的人’,只要叫得凶一点,也多少分一点给他们堵住嘴巴。” 另一位就是前一天晚上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至少十五年内不要提上日程的先生,他是一个巨型国有企业的党委副书记,年纪大概也就在四十岁左右,仕途远大。因为Z、X两位没有听到这位先生发表看法,于是我请他详细谈谈他的见解。这一次他除了谈了政治体制改革会带来苏东国家那种巨大的社会冲击,使我国陷入政治高度不稳定之外,还陈述了中国现在不适宜实行民主政治的种种理由,最主要的理由是中国民众素质很低,给了权力也不会用。中国的传媒确实需要管制,我们与西方的国情不一样,如果在中国这样的国度实行西方国家那种新闻自由,岂不乱套了吗?总之,中国现在的政治体制非常好,不需要进行深层改革,一旦改革,只会更乱。因为他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且看过不少书的人,谈的过程中还要引经据典,其理由之充分,让我们三人听得目瞪口呆,面面相觑。 L先生最善谈,而且一套一套。他先根据他的亲身经历,谈了一个“一把手不贪污”理论。他说,凡是他所到过的所有地方,一把手是不贪污的,因为这些人有责任心,这个地方是他的;犯错误的全是二把手以下的官员。然后列举了他所见到过的清官,如某县委书记是如何清廉且勤政爱民,而他在那里做成的任何生意,都是真本事干出来的,没花一分钱用在行贿上面。列举完种种事实后,他直接批评说我的《现代化的陷阱》那部书太偏激,将官员们讲得太坏了,“其实还是有不少清廉勤政的好官,我所接触到的官员,大多都是这类官员。我赚的每一分钱,都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