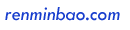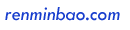【人民报讯】
【夜光新闻: 2000-11-11】华商报讯,我们生活的这个都市里,有一群专事陪舞的女人,她们来自全国不同城市和农村,大多只有初中或小学文化,背景不同,年龄各异,为了各自的目的,她们在黑暗中抛开了自尊———
10月25日至11月9日,本报记者正元经过充分准备,走近“陪舞女”这个特殊的人群,在她们“上班”和居住处与陪舞女交往16天,掌握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走近陪舞女 时间:10月25日下午2时30分——下午6时40分。地点:西安市西大街康乐舞厅、含光门外环城公园。 从小南门拦下一辆奥拓的士,上车后我表明要找个地方跳舞,40多岁的的哥端直将我拉到位于市中心繁华地段西大街康乐舞厅(事先“踩点”时已知道这里就是陪舞女“上班”的地方)门前,“就是这。”付钱时我看到的哥露出意味深长的怪笑。 舞厅里光线昏暗,弥漫着呛人的烟味、汗味和说不出的怪味,让人透不过气来。过了一会儿眼睛才慢慢适应。这时隐约可以看到,并不宽敞的舞厅里挤满各样的男人和女人,两边的座位早已没有虚席。我挤到一处靠近舞池的地方站住。一位“大姐”模样的老女人上来搭话:先生,跳舞不?一曲10块钱,如果跳全场,共8个黑曲子(指黑灯舞),给50元小费就行了。我摇头表示不会跳舞,“大姐”把脸贴得很近,“小弟,现在哪儿还有不会跳舞的男人?别骗大姐了,不就几十块钱嘛。真的不会,大姐教你。”随后拉着我的手几乎是强迫地将我拉进了舞池。 灯光逐渐暗淡下来,几乎一片漆黑,“大姐”抱紧了我。舞池中的人都像醉酒一样摇摇晃晃,谁也看不到谁的面孔,只能听到衣服的磨擦声、急促的喘气声以及不时发出的男人和女人的呻吟声。 一曲终了,很多男人给女人掏出好像早已准备好的10元零钱,我也一样给“大姐”掏了10块钱。 来到这里的男人不需要主动找舞伴,站在一旁不动就会有女人不停地跟你搭腔。我和一位二十五六岁的女人跳了两曲后,假装有点不舒服,并问她能否一起出去走走。女人问到哪里,我说随便哪都行,女人先是犹豫一会儿,又看了看我,最后表示同意,我们坐出租车来到含光门外环城公园。 “你为啥敢跟我出来,不怕我是个人贩子把你卖了,是条色狼把你吃了?” “不怕。”“为啥?”“我看你不像那种人。” 我们走在公园的林荫道上,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这女人好像放松了许多。在近一个小时的交谈中得知她叫赵红,今年4月份来的西安。为避免惊动她,我没敢问得太多。分手时,赵红主动给我留下了呼机号码,“你是个好人,以后不要到那个地方去了,会学坏的。” 赵红——处处陷阱不由人 时间:10月28日下午6时——当夜12时。地点:钟楼广场、南大街肯德基店。第二次见赵红是我给她打传呼约的,我们在钟楼见面,当时她满脸的不高兴,我问咋回事,她说:“男人真他妈的坏,跳了舞不给钱,气死我了。”“你不能乱骂人啊,我可没惹你。”待她逐渐消了气,我说:“今晚我请客,你想吃啥?”经过商量,我们来到南大街的肯德基店,在二楼找了个靠近窗子的位置对面而坐要了两份3号套餐外加一盒土豆泥、一份汉堡。饭桌上气氛不错。赵红说这是她来西安后吃得最香的一顿饭。她是个清新而爽朗的女子,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 我是去年3月27号从家里出来的,当时在连云港云台区一家饭店做服务员,对饭店的情况也不了解,刚干了3天,饭店出了事,公安局把饭店所有人都抓了起来,后来我才知道,这家饭店里面有很多“小姐”,她们都干那个。我稀里糊涂地被送进了劳教所。当时我真想不通,两次想自杀都被劳教所的干警发现。后来,觉得这样死掉反而不好,至少对不起养我的爹妈,我也就逐渐平静了,拼命地干活,积极表现。今年2月1号得以提前两个月释放。该过年了,我不敢回家,就到一个同学家过了年。这同学很够意思,借给我300元钱,我准备离开连云港,可我一个弱女子去哪儿呢?我想起了劳教所里认识的一个叫江娜的女孩,江娜是西安人,当时她告诉我西安挺好的,钱也好挣。2月底,我来到了西安。 我拨通了江娜留给我的电话号码,才知道这是江娜姑姑家的电话。她姑姑很热情,告诉我江娜不在家,让我过去坐坐。我去了,在那儿还见到了江娜的父亲,交谈中得知江娜一直没回来,江娜的姑姑还悄悄告诉我,江娜父母早已离婚。我想让他们帮我在西安找份工作,他们说不太好找,吃过午饭,我告辞。又去火车站打算离开西安。买车票时发现身上仅有的100来块钱丢了。我手足无措,哭了起来,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看我可怜,给了我300块钱。他是去南昌的,说如果我肯跟他去,他可以在南昌帮我找工作。反正我也无处可去,就跟着这个“好心人”走了。到了南昌,他在一家旅馆开了间房子,让我和他住在一块。我早就料到会发生这种事,丝毫没觉得意外,假意答应,瞅个机会就溜了。 3月上旬,我又回到西安,当晚住在火车站附近一家小旅店,公安查房,我没带证件,被送进收容所。几天后就出来了。无奈,我又找到江娜的姑姑家,真是前世冤孽,居然又在这儿碰上了江娜的父亲。这一次他表现得尤其热情,把我领到朝阳小区附近,找了间民房住下,他答应次日帮我找工作。第二天,他真的带着我跑了一天,没找到合适的活。就是那天晚上大约11点钟,他敲门说有事,我打开门,他就表现出了臭男人的贱德行,对我动手动脚。我扇了他一个嘴巴,刺激得他更加疯狂,扑上来把我按倒在床上,接下来的事不用说你也猜得出来。 3天后的一个下午,他把我带进舞厅,也就是我现在呆的地方,让我在那儿陪舞赚钱。开始,我真的觉得好屈辱,为了摆脱这个家伙,为了活人,我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听天由命,在这儿干。渐渐地也就习以为常了。其实,在这儿陪人跳舞,钱倒是来得很容易,如果运气好,一个下午加半个晚上能挣100来块。 “后来,我在舞厅认识了一个小伙儿,他对我挺好,每次出手都很大方。再后来我们同居了,他答应和我结婚,我能感觉到他在骗我,但我确实需要他,别误会,不是那种需要。我在我们家是老大,父母和弟弟妹妹都看着我呢,我这么长时间没回去,他们肯定担心。我想过年的时候把他带回家,在家里人面前证明我在外边过得还不错。对老人是一种安慰,对弟弟妹妹也是一个“榜样”。 刘晓雪——我也有我的爱 时间:10月29日——10月31日 地点:西安市西大街火凤凰歌舞厅、电子城刘晓雪住处。这几天,我几次进入舞厅,都是叫刘晓雪陪舞。她说我这人挺守规矩,一看就不是那种不三不四的男人。几天下来,我们便混熟了。 刘晓雪是四川万县人,今年只有19岁,自称来西安7个月,先前给别人做钟点工,在火凤凰的陪舞生涯尚不足两月。她相貌一般,性格比较外向,舞厅里的姐妹们都叫她“川辣椒”,她爱穿一身黑衣服,不喜化妆。她的客人很多,有时候她也给姐妹们介绍生意。 刘晓雪是这次暗访中给我最大震撼的陪舞女。 10月30日上午10时许,刘晓雪突然给我打传呼,说有几个朋友到她那里吃饭,邀我一块过去。我按照她说的地址在电子城附近一栋二层楼上找到她。她正在洗脸。这是一间不足10平米的旧房,听她说每月房租是80元。房内只有一张床、一个煤气灶、一个脸盆、几副碗筷。 吃饭过程中,刘晓雪的一个姐妹王某突然问刘晓雪:“你甘肃的小弟现在怎么样了?”刘晓雪一愣:“今天几号了?”我说是10月30号,刘晓雪“哎哟”一声,说:“我差点忘了,天天忙啥子吆!该给他寄钱了。”我说:“你不是四川人吗,怎么在甘肃还有个小弟?”她笑笑,没吱声。吃完饭王某说有事,就急急忙忙地走了。我又问刘晓雪甘肃小弟的事,“干么那么神秘?”她当时还是没解释。一个小时后,她向我下了逐客令:“你可以走了,我还有事呢。”我说:“咱们一块走嘛,反正我下午也没事,和你一块去办你的事。”她答应了。我们一块来到含光路北段邮局门口,她让我在外边等她一会儿,说给家里寄封信,就进去了。我等了一会,不见她出来,也走进邮局。她正趴在柜台上填写汇款单。我说:“你很孝顺嘛。”她又笑了笑,接着我发现汇款单上的收款人地址是“甘肃省会宁县××乡××村张刚弟弟收”。汇款金额是200元。待她办完手续,我说:“你不是四川的吗?怎么弟弟在甘肃,还姓张?把我都搞糊涂了。”她说:“你知道那么多干啥?”我故意表露出不满:“你要是把我当朋友就别瞒这瞒那的。”她犹豫了一会儿,说出一番令我大为意外的话: “张刚是一个很可怜的小孩,从小就没了爸,家里很穷,没钱上学。几年前我在家从报纸上看到一篇‘希望工程’救助活动的文章,知道了他的情况,就一直想办法帮助他。都快三年了。” 我很震惊,将信将疑。为了搞清这件事的真假,次日,我再次来到刘晓雪的住处,看了张刚写给她的几封信,这些信都是由房东“收转刘晓雪大姐”的,内容都是收到汇款,汇报成绩,表达了一个受资助儿童的感激之情。读着这些信,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刘晓雪说,有时候翻着这些信,可以感觉到一点生活的动力,觉得这世上还有人真心感激自己,需要自己,陪舞带来的屈辱感会多多少少得到一点消减,心理也会稍微平衡。 周素苗——无耻的“舞厅油条” 时间:11月2日——6日 地点:西安市西大街火凤凰歌舞厅、东大街骡马市、西关正街南小巷周素苗住处。周素苗是这次暗访中唯一猜到我真实身份的陪舞女,她不在乎我采访她的经历,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用化名。 这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女孩子。第一次她来邀我跳舞的时候,突然说:“你挺规矩的,根本不像来这儿玩的,你不是公安就是记者。”我半开玩笑地说:“你说是就是吧。”不知是出于一种与生俱来的直觉,还是长久经历练就的敏感,之后几天的接触中她就认定我是记者了。 她说,她是湖北孝感人,21岁,在火凤凰、康乐已干了13个月的陪舞女。两年前她在老家谈过一个男朋友,因为家里穷,连件像样的衣服都买不起,和男友见面时,还是借了邻居家女孩的一条裤子,家里来了外人,连个像样的凳子都没有。穷日子受够了,就跑出来打工,她先去了广州,在一家玩具 |